庆历年间的开封府,鸣冤鼓被擂得震天响时,堂上端坐的官员总会先盯着案上的砚台。 景祐五年春天,包拯在礼部贡院拆开进士榜单,名字排在甲科前列。 放榜官拍着他的肩说等着去大理寺当评事吧,他却把任命状折成了方方正正的小方块。 我爹娘今年都七十多了,他对着前来道贺的同乡说,转身回了合肥乡下。 这一去就是十年,直到父母相继离世,坟前的草换了三茬,他才重新拿起官印。 赴任端州那天,船刚靠岸就见衙役们抬着礼盒候着。 打开一看,十多方雕着龙凤的端砚码得整整齐齐。 大人刚到,这点心意……为首的县丞话没说完,就见包拯把自己带来的旧砚台摆到桌上。 那砚台边角磕了个缺口,还是他考学时用的。 后来端州的砚台贡额从三百方减到五十方,离任时他的行囊里,只有那方缺口砚台。 开封府的正门原来总关着,百姓递状子得绕到侧门,被胥吏刁难是常事。 包拯上任第三天就命人卸了正门的门栓,以后谁要告状,直接从这儿进来。 第一个推门进来的是个卖炭翁,手里攥着被抢走的炭票子,哆嗦着不敢上前。 包拯把案上的砚台往他面前推了推,写,不会写我替你记。 那天开封府的墨用得比往常多了三倍。 嘉祐三年的早朝,包拯盯着站在仁宗身边的张尧佐,手里的笏板捏得发白。 这位贵妃的叔叔刚被封了四个要职,满朝文武没人敢作声。 他突然往前迈了三步,声音震得殿上的琉璃瓦都像在颤,三司使掌管天下财赋,张尧佐连账本都看不懂,陛下是要让天下人戳朝廷的脊梁骨吗?唾沫星子溅到仁宗脸上时,他还在念着百姓交不上赋税的苦。 民间总说他额有月牙能断阴阳,我觉得那月牙更像把尺子,量过端州的砚台,也量过开封府的大门,量的都是人心的公道。 现在去端州,还能看见当年他定下的贡砚石碑,字里行间都是不与民争利五个字。 开封府旧址的正门改成了博物馆的入口,游客走进时总会下意识抬头,好像还能看见那个黑着脸的官员,正把百姓的状纸往砚台边挪了挪。 把规矩刻进骨子里,让公道看得见摸得着,这或许就是千年后我们依然记着他的原因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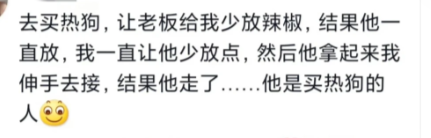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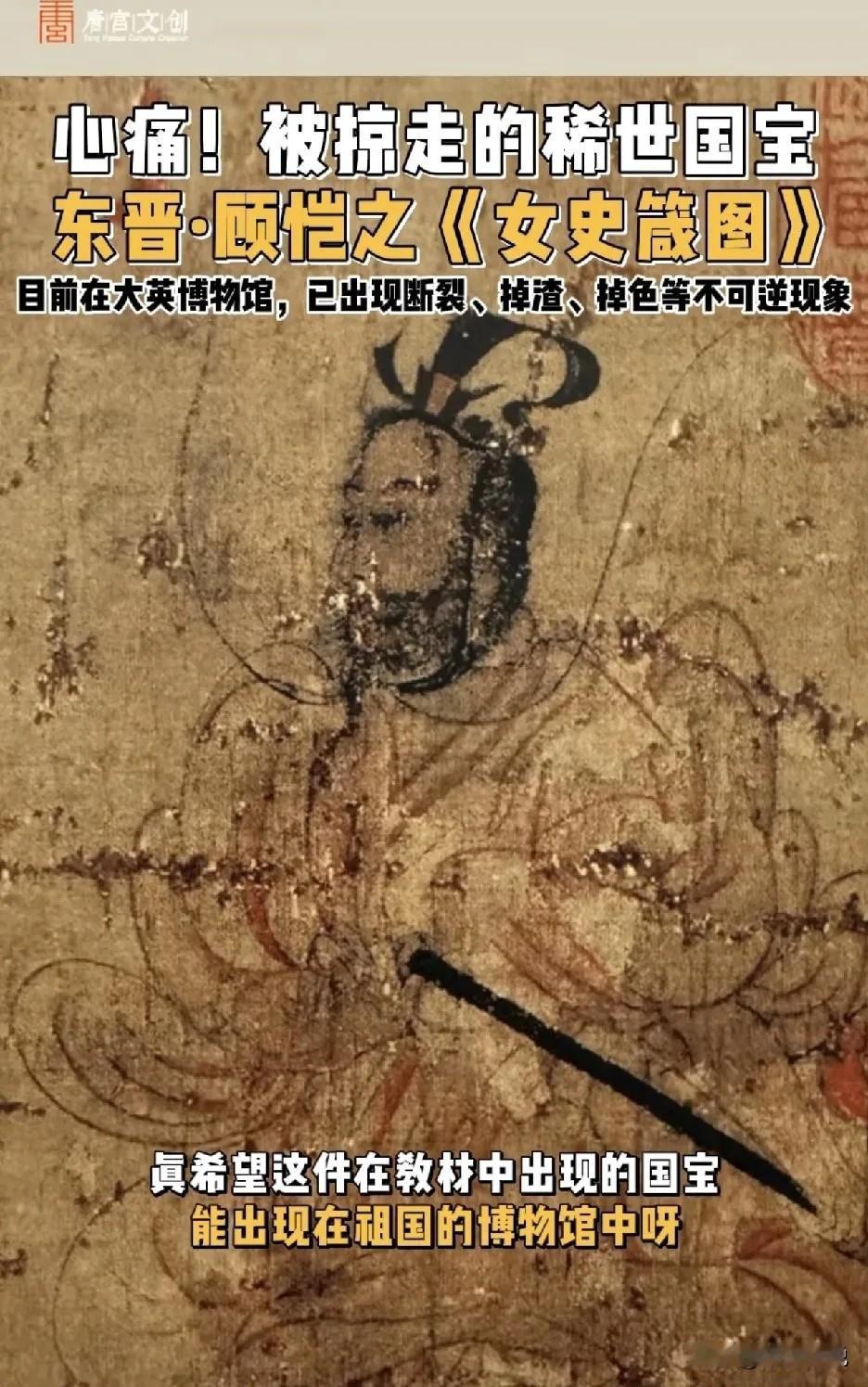


![[红脸笑]终于能把心放肚子里了,莎莎这脚踝伤总算有了准信儿!](http://image.uczzd.cn/6571573190066034845.jpg?id=0)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