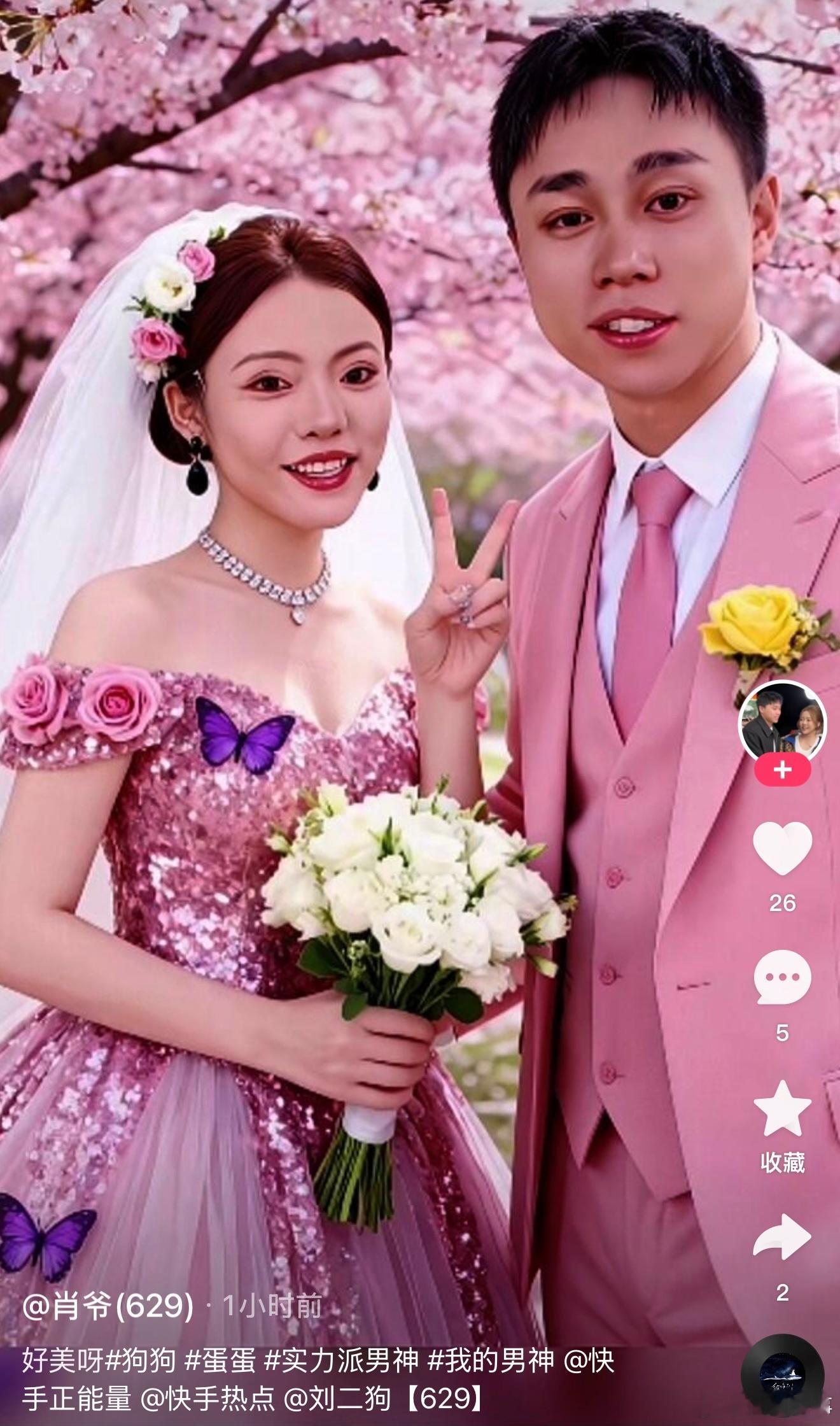我一远房表姐,人特别善良,收养了好几只流浪猫狗。可她对自己亲妈特别刻薄,经常大吼大叫,不给好脸色。她说:“我妈重男轻女,毁了我前半生,我对小动物好,是因为它们不会像人一样坏。”表姐住的老小区一楼,阳台改造成了猫狗的小窝,铺着旧毯子,摆着好几个食盆水盆。 老小区一楼的阳台总飘着猫粮混着旧毯子的味道,三花猫蜷在褪色的绒垫上,尾巴扫过搪瓷食盆,发出叮当响——那是表姐每天雷打不动的“投喂时间”。 可推开她家防盗门,常听见她对着电话吼:“说了别来!你那点退休金留着给你宝贝儿子买酒去!” 电话那头是她亲妈,一个被她挂在嘴边“毁了前半生”的女人。 阳台栏杆上还搭着洗旧的猫窝,针脚歪歪扭扭,是她熬夜缝的——对这些不会说话的小生命,她总有无尽的耐心。 五年前她在垃圾桶旁捡到第一只瘸腿的流浪狗时,刚和家里大吵一架;那天她妈拿着她的工资卡给弟弟交了首付,理由是“女儿早晚是别人家的人”。 后来她把阳台封成猫狗的“小城堡”,却把妈妈送来的腊肉扔在门外:“别用你的东西脏了我的地方”;妈妈站在楼道里,塑料袋被风吹得哗啦响,她头也没回。 转折发生在去年冬天,她半夜带发烧的猫去宠物医院,急诊室里撞见同样挂急诊的妈妈——老人攥着皱巴巴的病历本,羽绒服袖口磨出了毛边,看见她时,眼里的光闪了闪又灭了。 有人说她冷血,可谁见过她给流浪猫擦眼睛时,指尖轻得像怕碰碎玻璃?谁又听过她喝醉后嘟囔:“要是小时候我发烧,她也能这么抱着我去医院就好了”——或许刻薄不是本意,只是她给自己砌的墙,墙里是没被爱过的小女孩,墙外是不敢靠近的母亲。 重男轻女的标签像根刺,扎在她二十多年的人生里;妈妈一次次把资源倾斜给弟弟,让她觉得“我的感受从来不重要”;于是她把情感投射到不会评判、不会背叛的动物身上——它们饿了会叫,冷了会蹭,给点温暖就摇尾巴,这种“确定性”,是她在原生家庭里从未得到过的。 现在她还是会对妈妈说重话,但会悄悄把妈妈放在门口的饺子收进冰箱; 阳台的猫狗多了三只,她眼角的细纹里,多了点连自己都没察觉的松动; 或许和解从来不是“原谅”,而是承认:那个被亏欠的小女孩,值得被看见——哪怕先从看见自己开始。 夕阳把阳台的影子拉得很长,三花猫跳上窗台,隔着玻璃望屋里;表姐正给猫梳毛,手边放着那袋没扔的腊肉,袋子上还沾着妈妈指纹的温度。
我一远房表姐,人特别善良,收养了好几只流浪猫狗。可她对自己亲妈特别刻薄,经常大吼
昱信简单
2025-12-21 14:51:41
0
阅读: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