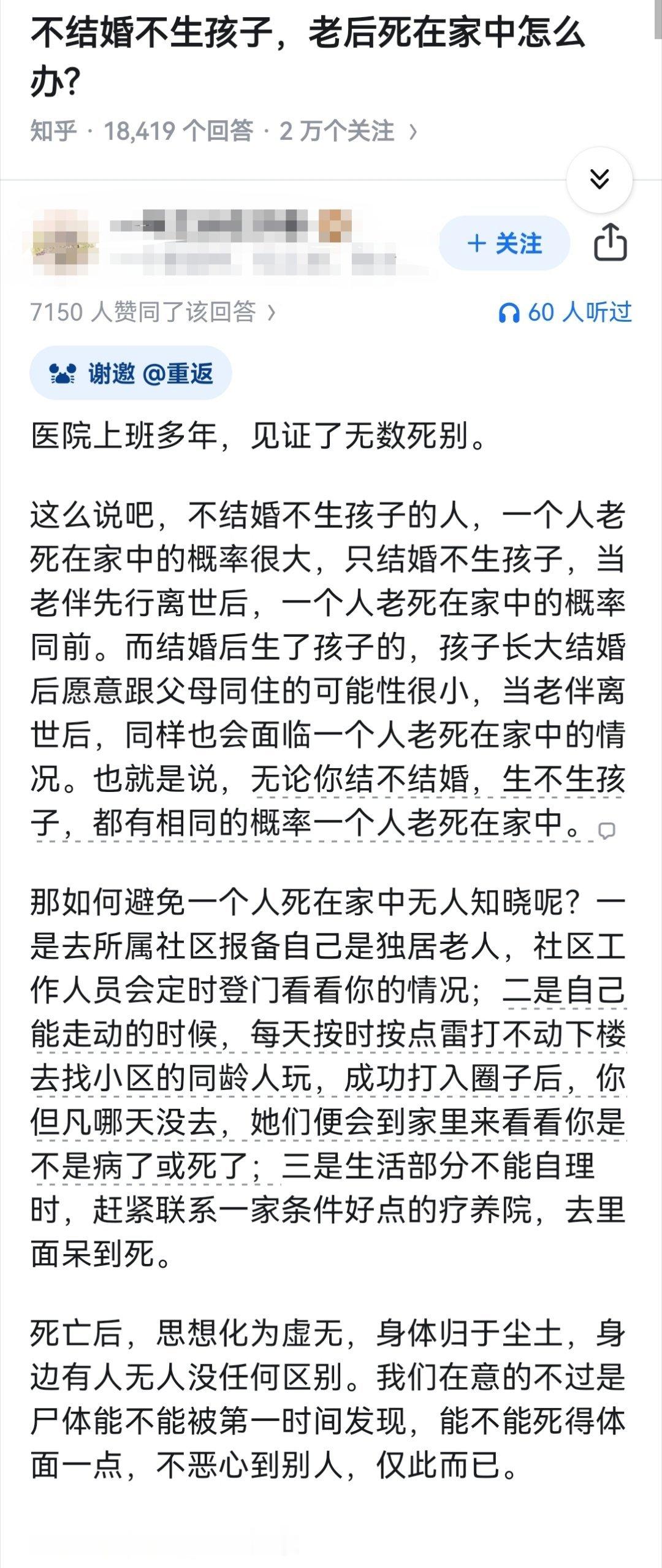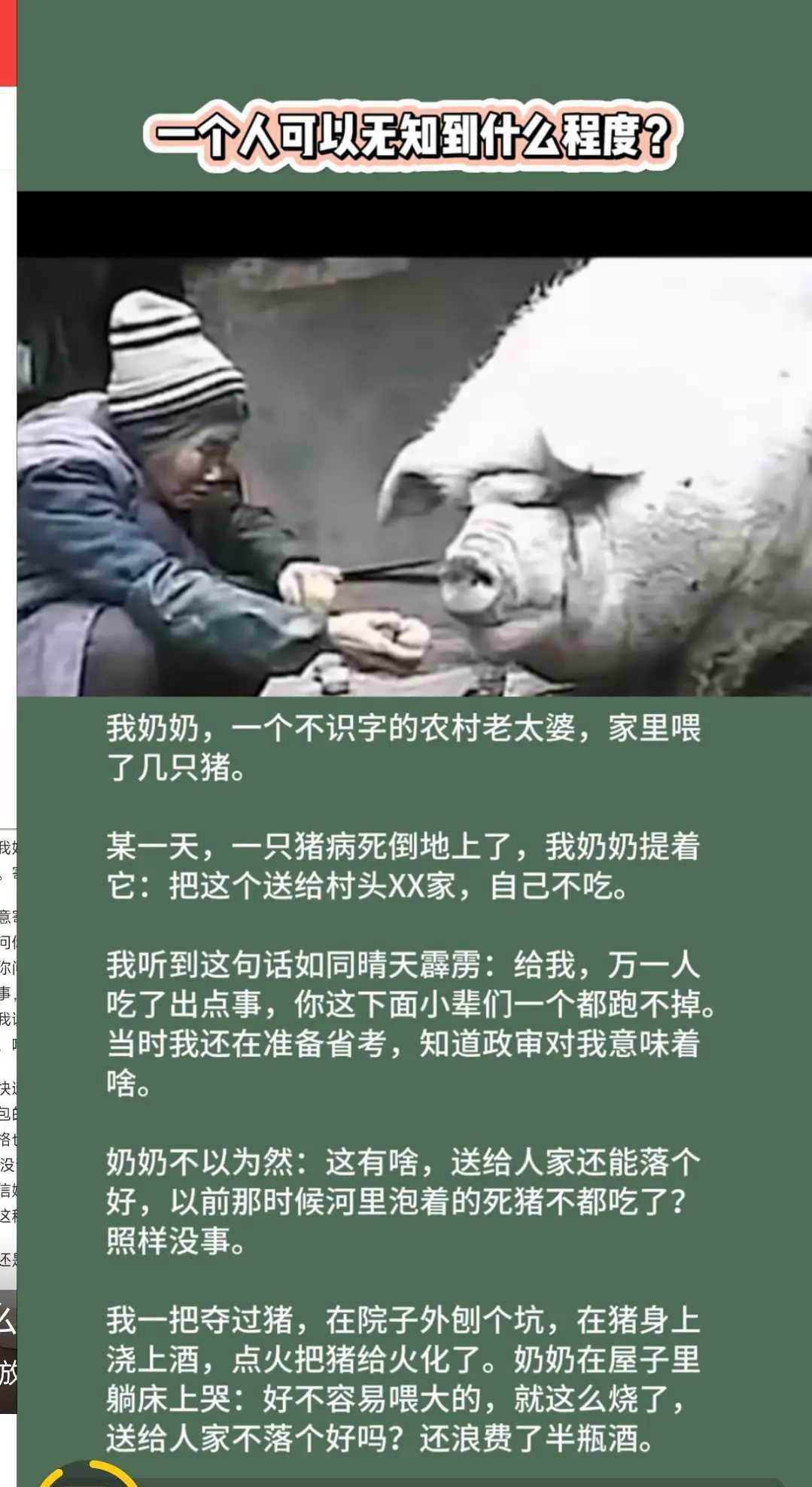儿媳妇没有想到,她骂了我后,我直接放弃她了,从她怀孕生孩子,我都没有参与,因为,她说过,她不想看见我,我不在乎她记仇,什么月子仇,什么一系列记仇,报仇,都无所谓。当初她刚怀孕那会,儿子还劝我去照顾她, 我攥着手里的毛衣针,线团在脚边滚了半圈,停在电视柜的裂缝旁——那是去年冬天,她摔门时带倒的花瓶砸的,瓷片溅到我鞋尖,她没回头。 她刚查出怀孕那月,儿子拎着一篮草莓来我这儿,草莓蒂上还挂着水珠。他把草莓放在茶几上,手指摩挲着篮沿:“妈,你去看看她吧,孕吐厉害,吃不下饭。”我没接话,把草莓洗了,装在她以前最喜欢的白瓷盘里——那盘子是她刚嫁过来时,我俩一起去菜市场淘的,她说上面的蓝牡丹像我种的那盆。 我提着盘子站在她家门口,门没关严,听见她跟儿子吵:“你妈能不能别总来烦我?上次她说要给孩子织毛衣,颜色土得掉渣,她是不是觉得我离了她活不了?”我在门外站了会儿,把盘子放在脚垫上,转身时听见门“咔嗒”一声落了锁。 真正说开是在一个雨天。她来我这儿拿儿子忘带的文件,刚进门就看见沙发上搭着件小毛衣,奶黄色的,领口绣了朵小小的蓝牡丹。她突然红了眼,抓起毛衣扔在地上:“你能不能别装了?我早就说过,我不想看见你!你那些好心都是假的,你就是想控制我们!”她的声音混着窗外的雨声,有点发飘,“我看见你就烦,从结婚那天起就烦!” 我弯腰捡起毛衣,针脚被扯得松了几处。儿子从厨房跑出来,想拦,我按住他的手。“行,”我把毛衣叠好,放进柜顶的纸箱,“你不想看见我,那我就不出现。” 后来她肚子大起来,小区里的张婶碰见我,问:“你家儿媳快生了吧?不去照顾月子?”我正在给月季剪枝,剪刀“咔嚓”剪断一根枯枝:“她自己安排好了。”张婶撇撇嘴:“哪有婆婆不管的?小心记仇。”我笑笑,没说话——月子仇?记仇?这些词在我脑子里转了转,像风吹过空坛子,响了一声就散了,谁又真的在乎呢? 她生孩子那天,儿子半夜打电话来,声音哑着:“妈,她难产,医生问要不要家属进去……”我握着电话,听见那边传来婴儿的哭声,很小,像小猫叫。“让她妈去吧,”我说,“她想见的人,才管用。”挂了电话,我起身走到窗边,看见楼下的路灯亮着,光打在湿漉漉的地面上,映出我窗前那盆蓝牡丹的影子,花瓣上还沾着夜露。 前几天去儿子家拿我的老花镜,刚进门就听见小孙女在哭,儿媳妇抱着孩子在客厅转圈,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。她看见我,脚步顿了顿,没说话。小孙女哭得更凶了,我走过去,从口袋里掏出颗糖——是我出门时在小卖部买的,水果味的,包装纸上画着小熊。我把糖递到孩子眼前,她突然不哭了,小手抓住糖纸,咯咯地笑。 儿媳妇看着我,嘴唇动了动:“妈,上次……”我摆摆手,抱起小孙女,她的小手软软的,抓着我的衣领。“孩子叫什么名?”我问。“念念,”她说,“思念的念。”我低头亲了亲孩子的额头,她身上有股淡淡的奶香,像刚出炉的小馒头。 走出儿子家时,太阳正好照在楼道里,暖洋洋的。我想起张婶说的“记仇”,突然觉得好笑——人这一辈子,哪有那么多仇要记?不过是你多走一步,我少退一点,日子就过去了。就像我脚边这团线,滚远了,捡起来,接着织就是了。 线团还在电视柜旁,我弯腰把它捡起来,毛衣针上的线松了个结,我用牙咬断线头,重新起针。小孙女的毛衣要织快点了,天冷了,奶黄色的线,配蓝牡丹,应该会好看。
不结婚不生孩子,老后死在家中怎么办?
【1评论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