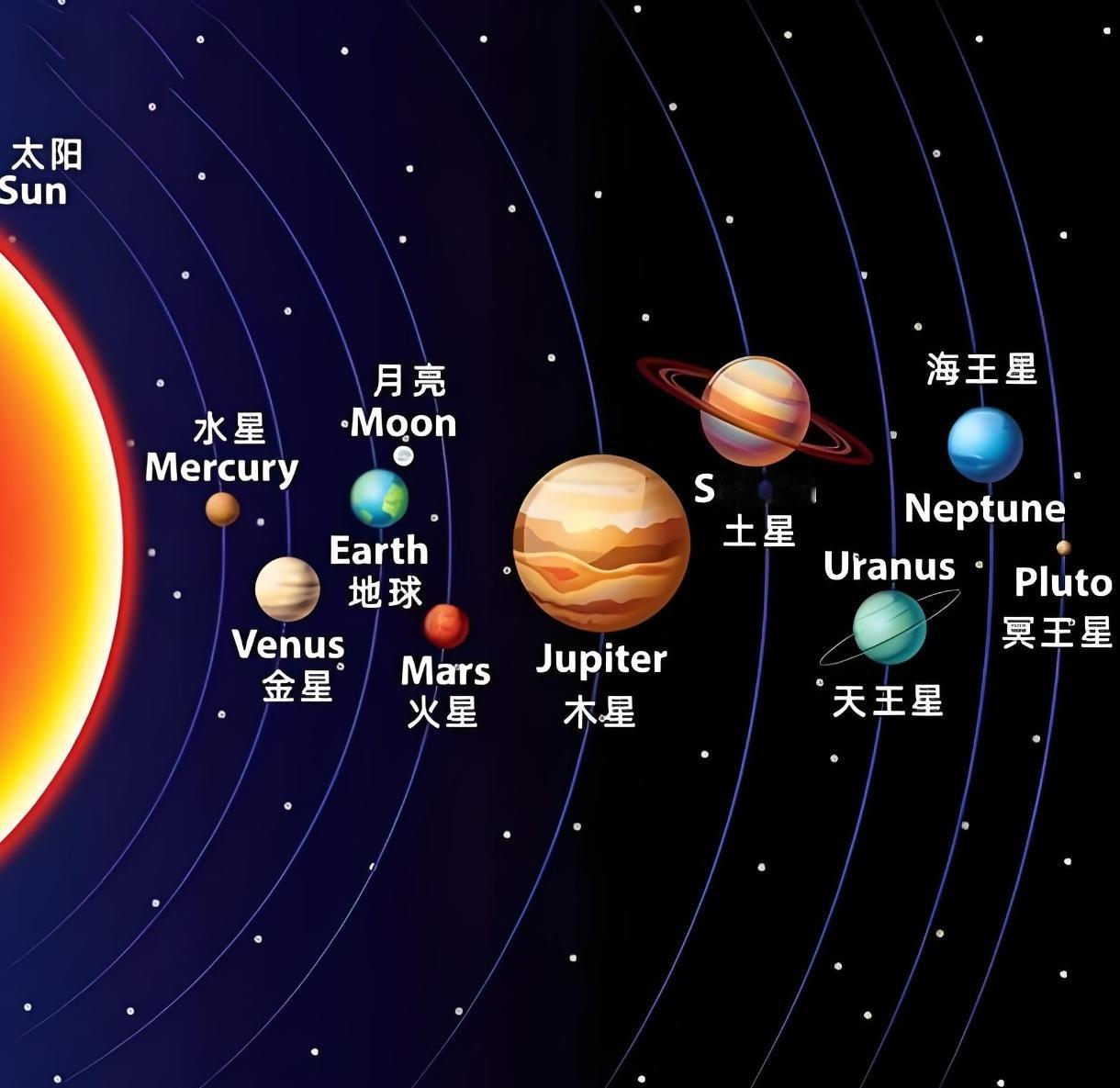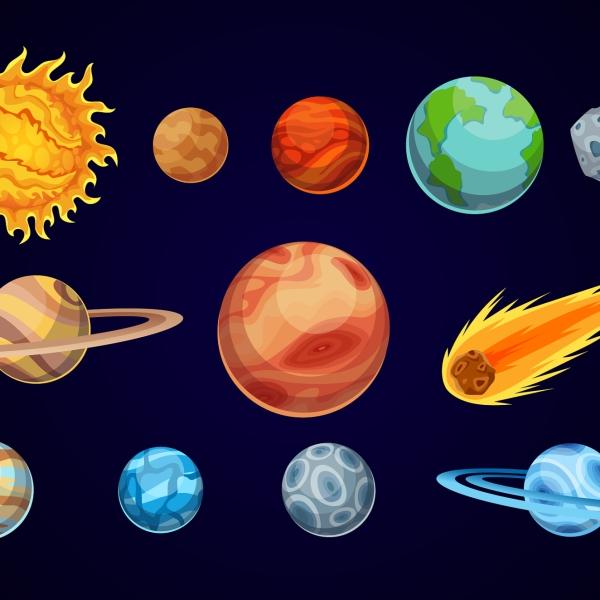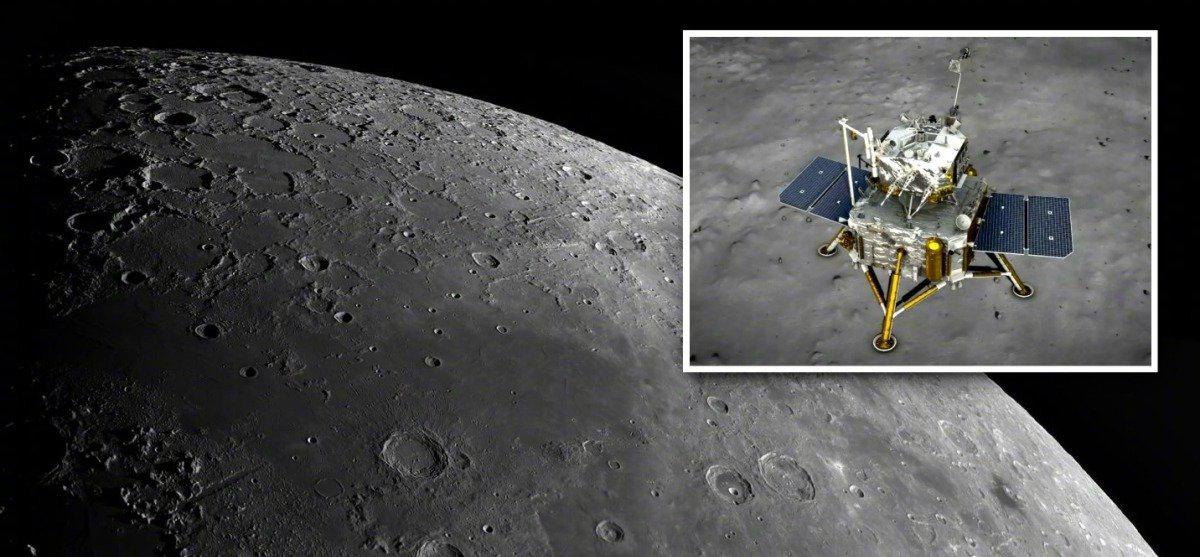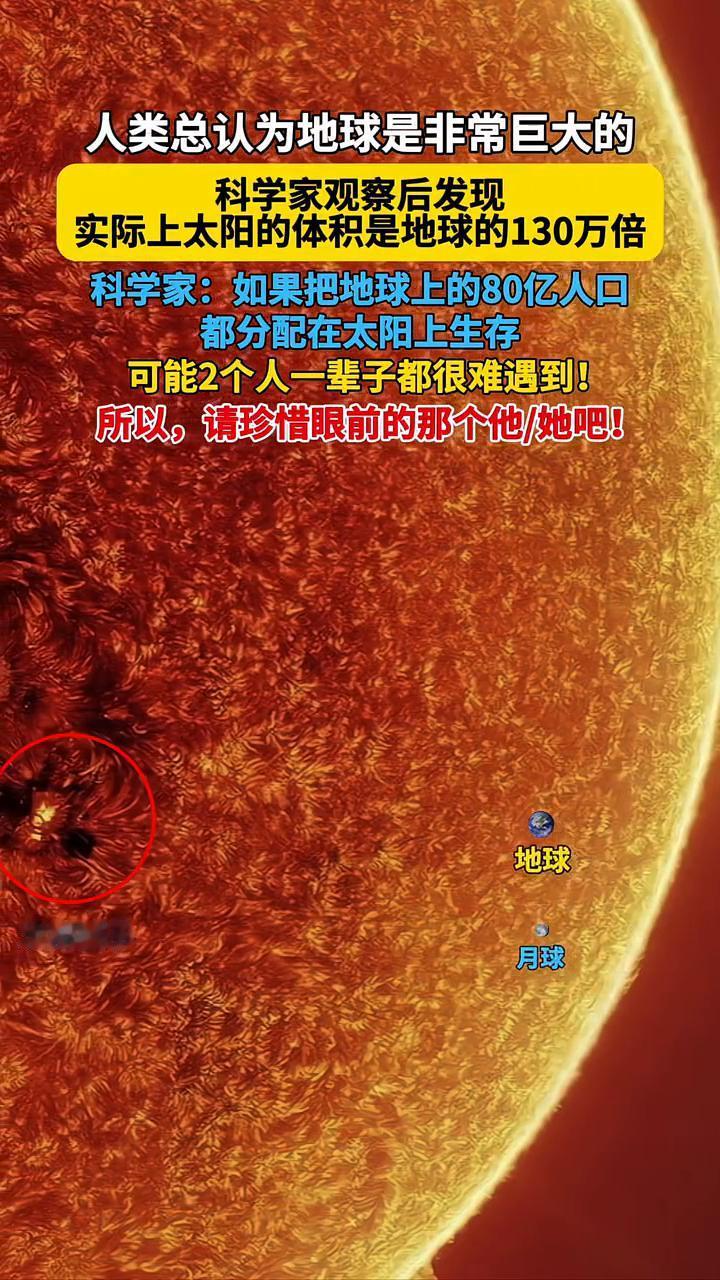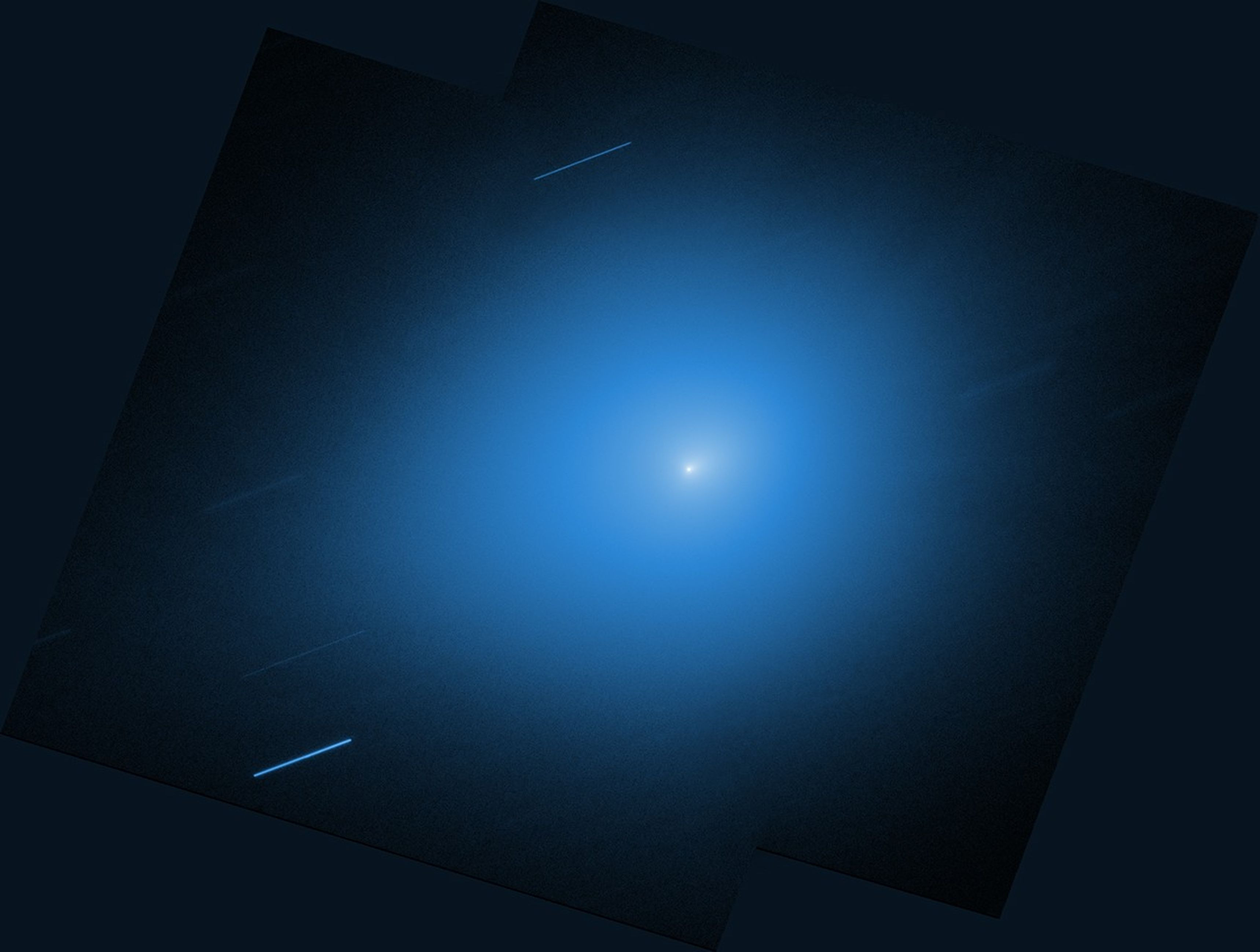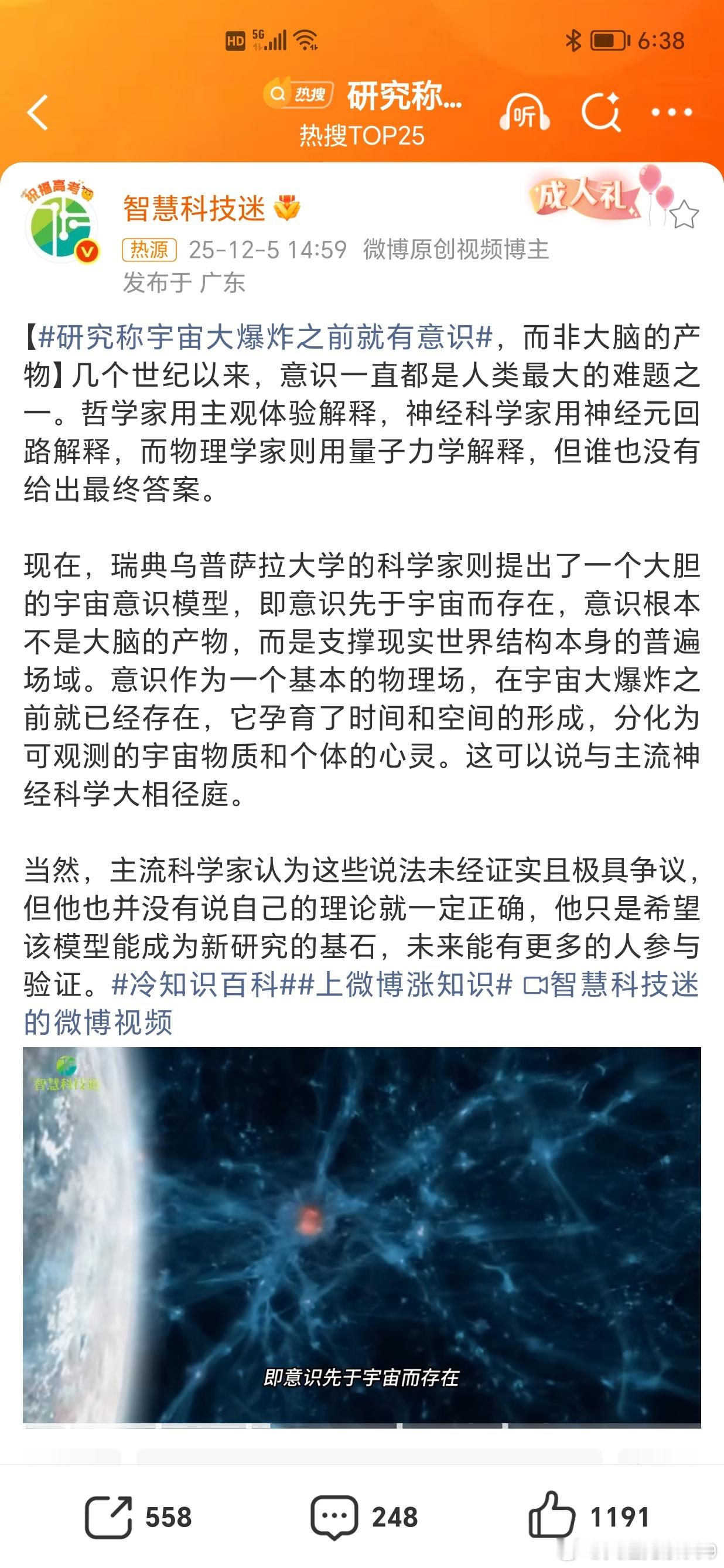地球上只剩两头,还都是母的,如果人工授精还不成功,人类可能再也看不到这个物种了 看到这句话,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:“真的假的?一个物种就靠两头母的了?”但现实比想象还要残酷。 北方白犀牛本不是濒危动物的“钉子户”,在上世纪60年代,这种体重两吨、长得像装了铠甲的庞然大物,在非洲草原还有超过2000头。 它们不是因为生态环境恶化、天敌变多才慢慢消失的,而是被人类直接“清仓处理”。 问题的根源两个字:犀角,在黑市上,犀角曾一度炒到每公斤6万美元,被当成炫富的工艺品,也被误传有药用价值,尽管科学已经反复说明它和人的指甲成分一样,主要是角蛋白。 但这并不妨碍市场疯狂,盗猎活动日益猖獗,尤其是在非洲一些地区政局混乱、执法力量薄弱的背景下,武装分子甚至用犀角换军火,盗猎几乎成了暴力经济的一环。 虽然犀牛的灭绝和盗猎绝对脱不开关系,但其实很多盗猎者本身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“坏人”,他们只是穷得没有别的选择。 在非洲一些经济落后、失业率高的地区,打猎换钱比种地养家来得快,比如,一公斤犀牛角能卖出几万美元,是当地人几十年都赚不到的钱。 你让一个每天吃不饱饭的人为了“生态理念”放弃这个机会,可能性有多大? 而在国际市场,犀牛角、象牙、穿山甲鳞片这些“野生奢侈品”长期受到部分国家高端需求的推动,有些被当成传统药材,有些被视为身份象征,还有些被炒作成投资品。 这条黑色产业链一旦形成,就不是靠一两个自然保护区就能断掉的,只要“买的人”还在,猎的人就不会停。 有保护区负责人公开承认,他们经常抓到盗猎者,但最后不是被轻判,就是压根没人起诉,抓了等于白抓。 有时候,刚抓进去几天的人,转头又出现在林子里拿枪找犀牛,这种“抓不怕、判不重”的司法环境,直接削弱了保护的威慑力。 在国际层面,野生动物保护也不是“众口一词”,一些国家呼吁全面禁止象牙、犀角等野生动物制品交易,另一些国家却认为这侵犯了他们的文化传统或经济权益。 还有些非洲国家主张“可持续利用”,认为只要是自然死亡的动物留下的资源,完全可以合法交易,用于发展本地经济。 这就造成了全球规则的不统一,一边在打击非法贸易,一边却又有人打着“合法”旗号出口动物制品,黑白界限被模糊,反而让执法变得更加困难。 到了1984年,野生北方白犀牛数量已经跌到了只剩15头,几乎就是崩盘式的下滑,2008年,这个物种正式“从野外毕业”,被宣布在野外灭绝。 更糟的是,北方白犀牛的生育能力本就不算强,加上长期圈养生活带来的各种生理问题,想靠剩下的几头繁殖后代,就像指望70岁的老夫妻再拼一胎,难度不言而喻。 在这个几乎被判死刑的物种中,曾经有一头名叫“苏丹”的雄性犀牛,成了人类最后的希望。 为防止它被偷猎,苏丹24小时都有持枪卫兵陪护,比很多政要还安全,但就算保护再周全,岁月不饶犀。 苏丹终究老了,到了2018年,它因为严重感染和起不了身,被执行安乐死,年纪45岁,这头老犀牛的离世,标志着北方白犀牛“自然繁殖”的大门彻底关上了。 现在还活着的“纳金”和“法图”,一个是苏丹的女儿,一个是外孙女,也就是说,它们是仅存的两头北方白犀牛,而且都不能自然受孕。 苏丹死后,它的精子被冷冻保存,成为科学家“人工繁殖大业”的唯一火种,可光有精子还不够,母牛的身体状况也必须能配合,而“纳金”和“法图”年纪也大,再折腾太多次取卵手术,对它们本身就是风险。 科学家当然没坐以待毙,自2019年以来,国际科研团队已经从“纳金”和“法图”体内成功提取卵子,并用苏丹冷冻的精子进行体外受精。 成功培育出的北方白犀牛胚胎被冷冻保存,计划未来植入南方白犀牛的子宫,让它们代孕,然而,这一切都只是“可能”,科技无法保证一定成功,更无法保证新生犀牛能正常发育、繁殖、适应环境。 而时间,是他们最缺的资源,纳金和法图都已进入高龄,卵子质量逐年下降,胚胎转移的窗口期正快速关闭。 这场科技救援,像是给物种续命的“心脏手术”,刀尖上跳舞,成败难料。可如果连这最后一搏都放弃,北方白犀牛就真的只能留在纪录片里了。 北方白犀牛不是第一个走到灭绝边缘的物种,可保护资源是有限的,而受关注的动物才拿得到“预算”,像北方白犀牛、雪豹、大熊猫这种“明星物种”,因为长得可爱、知名度高、容易吸引捐款和媒体曝光,所以能得到更多的保护资源。 但那些“长得不讨喜”的冷门物种,比如某种小型蛙类、稀有甲虫、濒危植物,往往连基本的生存数据都没有,更别提保护计划了。 信息来源:这个生物世界上仅剩两只,还都是母的,科学家:很绝望 ——光明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