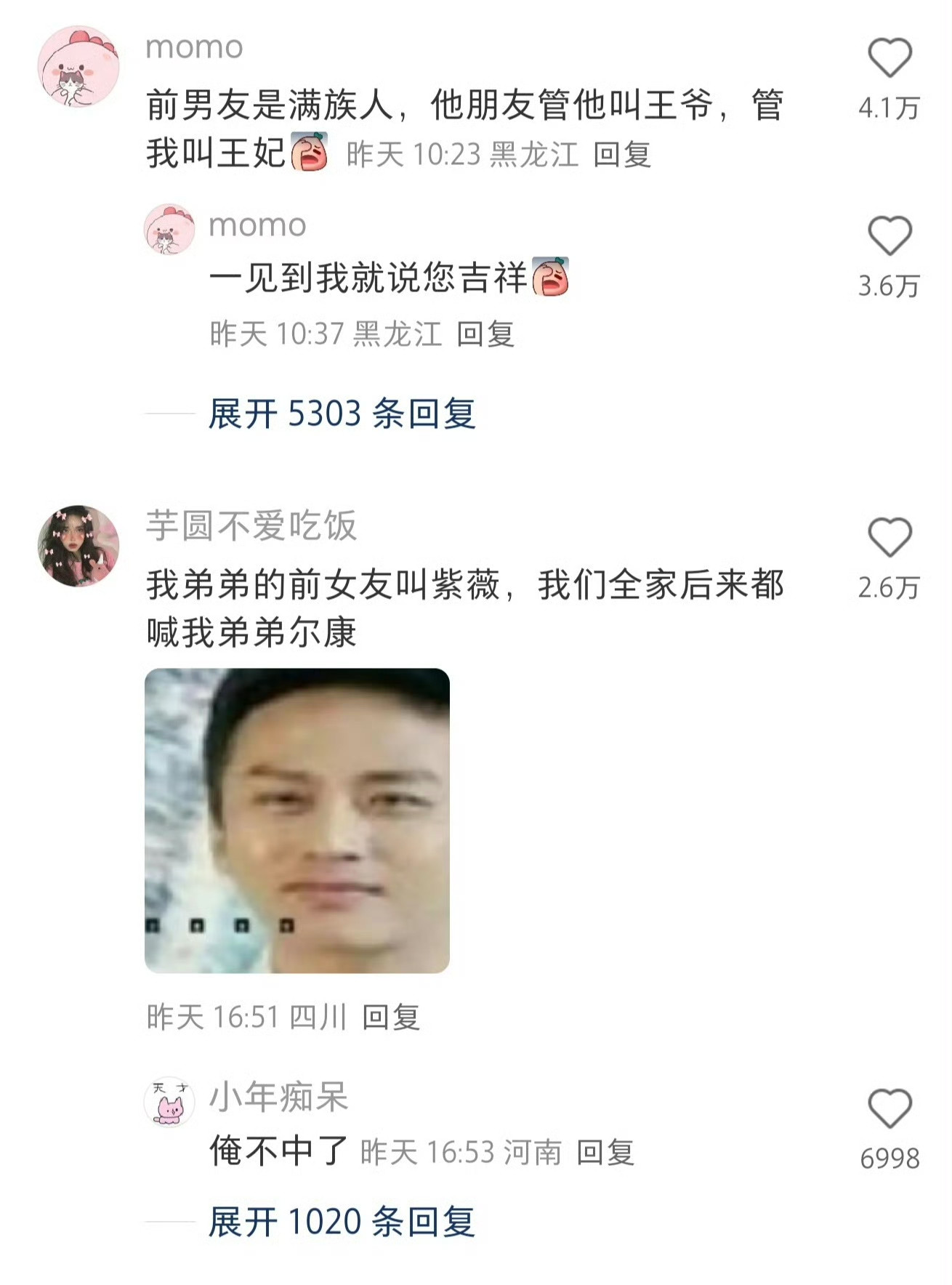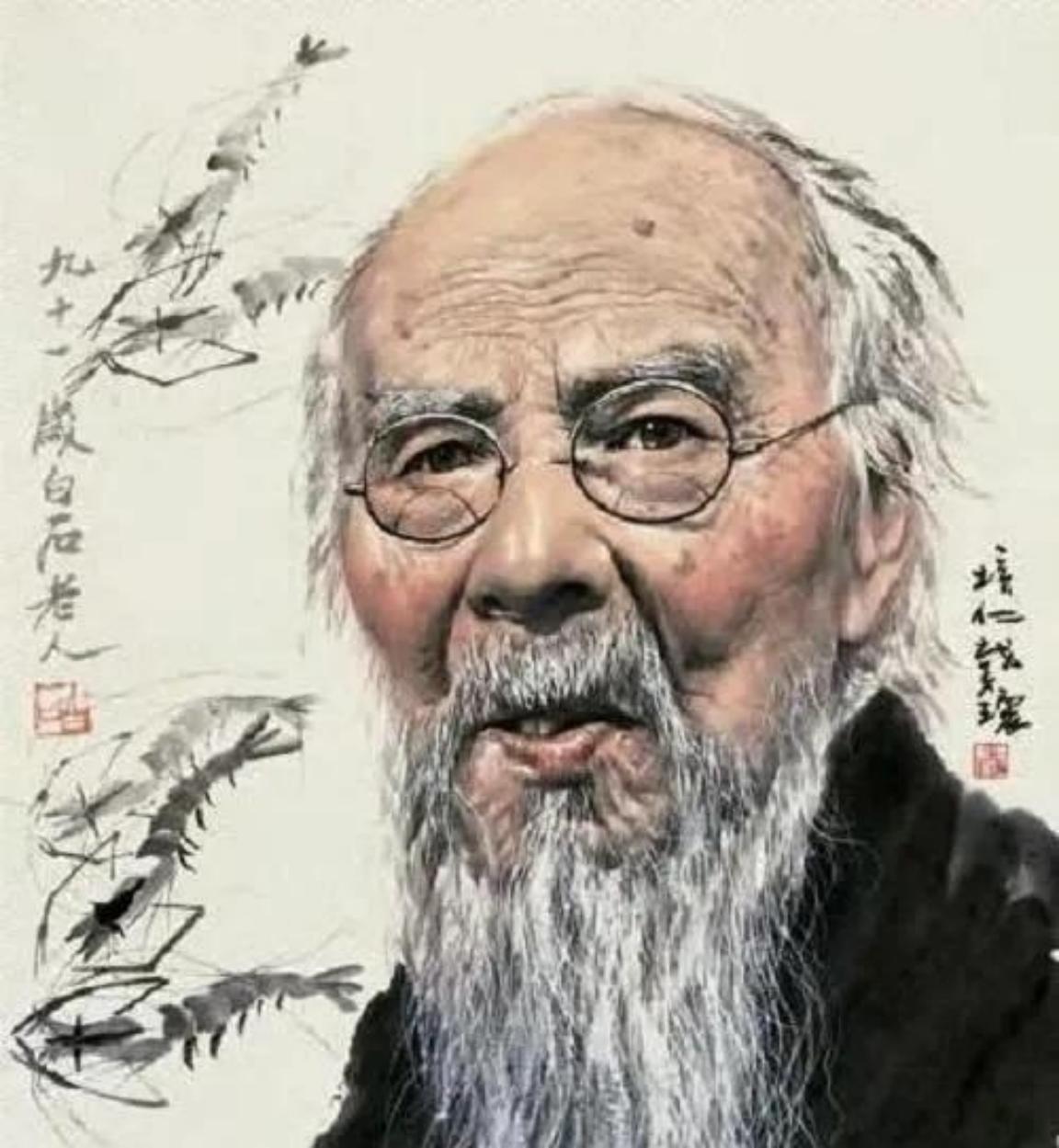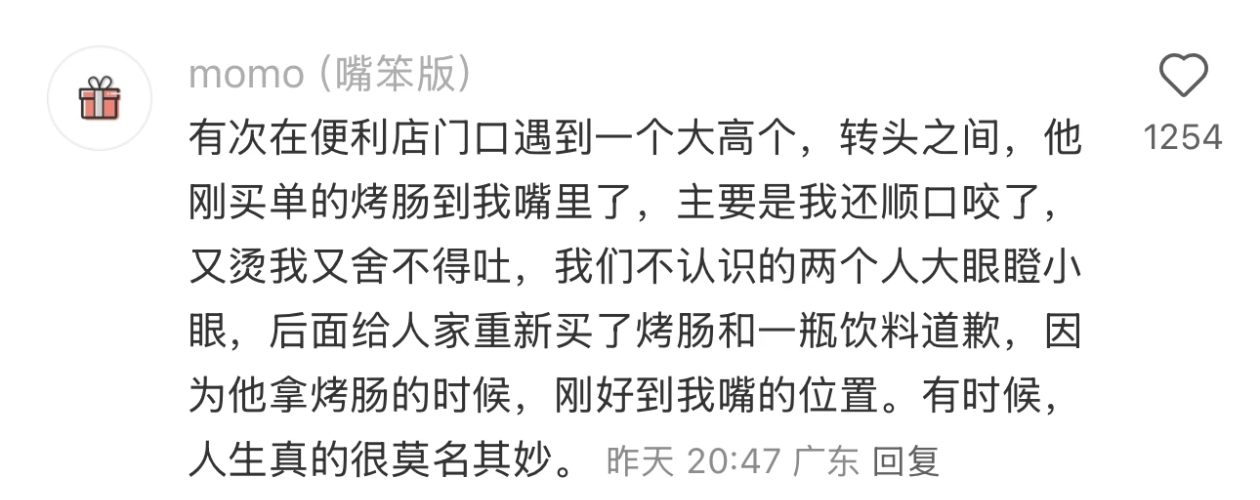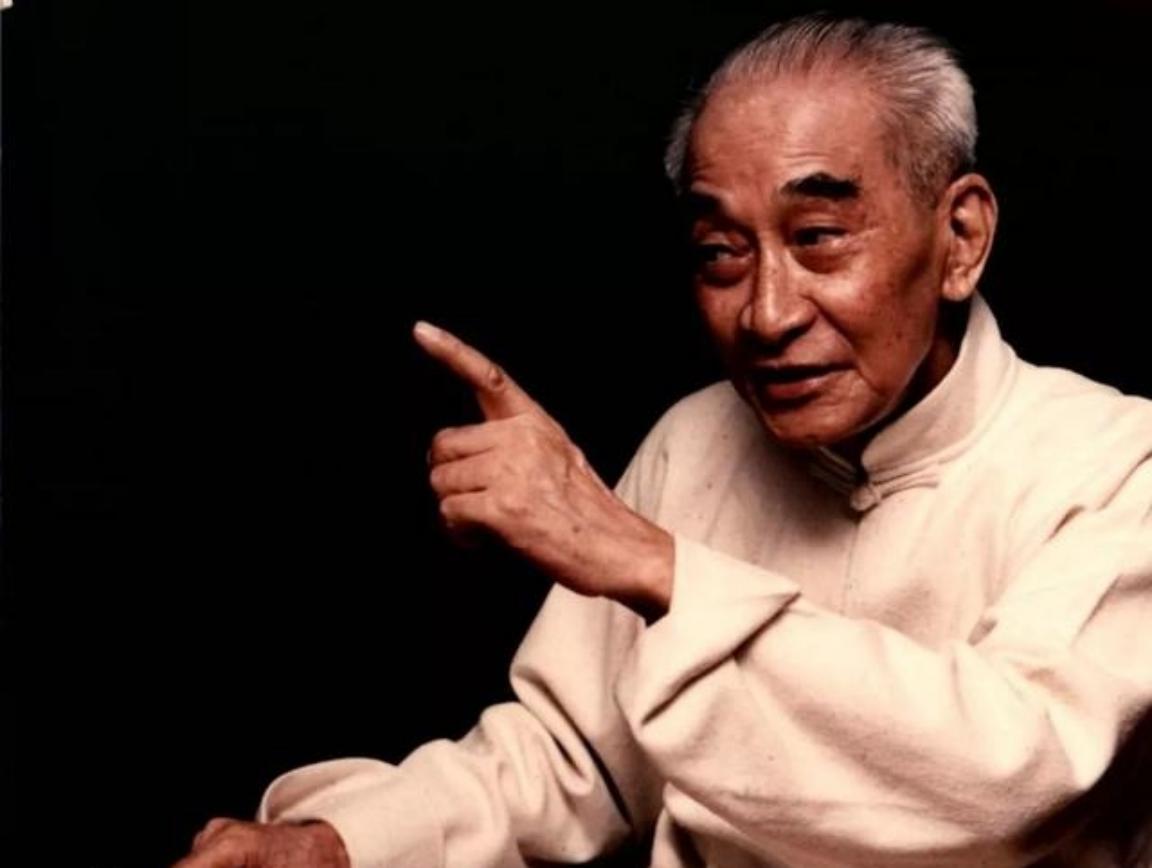1955年,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工以后,林徽因认为碑文应该用楷体来写,但具体由谁来写犯了难,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说:“周总理的字苍劲雄伟,刚劲有力,有如颜碑,风格端庄凝重,可以问问周总理”。 1949年9月23日,北平国立艺专的一位老师滑田友,给市建设局写了一封信。 他说,咱们得在天安门广场建座碑,给那些为国家牺牲的人一个交代。这不是突发奇想,他是早就憋着这口气了。 作为留法归来的艺术家,滑田友一向讲究民族性,信里提到,“要建,就得建得有中国味儿。” 没几天,毛主席就拍了板。9月30日,政协会议刚一结束,毛主席亲自带头,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奠基仪式。 那天,第一次奏响了后来成为国丧专用的哀乐。碑座也立了,陈志敬刻的,上头写着“为国牺牲的”几个字。 可惜,那个碑身后来失踪了,成了历史的一个悬案。 从那天起,这块碑就不是普通的石头了。它成了共和国的象征。 时间一晃到了1952年,纪念碑正式开工。这是个大工程,不光是建材和施工的问题,更大的难点在于:碑文怎么写、怎么刻、谁来写。 毛泽东早在1949年政协会议期间就写好了碑文。全文155个字,没一个标点,全靠断句和气势。 通篇分三段,从1840年讲到新中国成立,逻辑清晰,气势如虹。可毛主席只写文字,不写字。那怎么办? 林徽因这时候站了出来。她是设计团队的核心人物,一直主张碑文要用楷体。 她说得很直白,这种碑,不是拿来装饰的,是让人敬畏的,字体必须端庄肃穆。 她甚至坚持不用木棉花做装饰,因为“那是南方的花,得用咱们老百姓熟悉的花,牡丹、荷花、菊花,这才接地气。” 可问题来了,楷体可以,那谁来写? 这就回到了1955年那个夏天。大家都知道这事难。不是没人能写,而是没人敢写。 写得不够好,那是对英雄的不敬;写得太花哨,又会被批评为不庄重。这时候,彭真说那句话,其实是有点冒险的。 毕竟,周总理是政府的总理,不是书法家。让他来写,万一不合适,谁担得起这个责任? 可很快,大家都觉得他说得有道理。周恩来小时候学过颜真卿的《多宝塔碑》,后来又研究魏碑,字体早就练得炉火纯青。 南开校牌是他写的,“千古奇冤,江南一叶”也是他写的,那股子浑厚劲儿,别人真学不来。 于是,就去问了周总理。 周恩来听完没说同意,也没说不同意。他只是点了点头,然后回去练字去了。 这一练,就是四十多遍。据说那一摞废稿,厚得能当枕头。 他每个字都推敲,比如“垂”字,要竖画挺直;“朽”字,要撇捺舒展,不能有一丝马虎。 练到最后,他才拿出一张稿纸,说:“就这个吧。” 林徽因看完,说了一句话:“这字,能让人肃然起敬。”梁思成也点头,说:“纪念死者,鼓舞生者。” 1955年6月9日,毛主席亲自题写了正面八个大字:“人民英雄永垂不朽”。 这八个字,气势磅礴,像是从历史深处走出来的声音。而背面碑文,周总理题的那一段,则更像是沉稳的回响。 一刚一柔,一主一辅,形成了后来被称为“双绝”的书法作品。 可你知道吗?这段碑文里,“永垂不朽”出现了三次。 而周总理写的三个“永垂不朽”,每一个都不同,笔力层层递进。就像他心中对人民英雄的敬重,一层比一层深。 1958年5月1日,纪念碑正式揭幕。那天,广场上人山人海。 站在碑下的人,不一定知道背后的故事,但他们能感受到,那不是一块冷冰冰的石头。 那是用心、用汗、用敬畏写下来的“碑语”。 后来有人问林徽因,这块碑值不值得她花这么多年心血去设计。她笑了笑,说:“这不是一块碑,这是我们的根。” 现在你再看那块碑,它站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,面朝东方,背靠历史。不喧哗,不张扬,却比任何语言都能让人沉默。 一笔一划,写下的不只是字,更是共和国对英雄的承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