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谦被杀21年后,明宪宗朱见深问过周能一个问题。周能曾跟着于谦守北京,宪宗问:“于少保被冤枉时,为啥不辩解一句?” 周能的回答,让宪宗半天说不出话。 成化十一年深秋,紫禁城暖阁里,宪宗指尖划过《北京保卫战纪事》,“于谦” 两个字很醒目。 他抬头看向阶下的周能。老人头发胡子全白,背也驼了。 “周将军,你当年随于少保守德胜门,亲眼见他建功。可他被诬谋反时,为啥不辩?” 宪宗语气里满是困惑。 周能听到 “于谦” 二字,身子一颤,眼睛红了:“陛下,于少保不是不辩,是不能辩、不敢辩啊!” “那日在牢里,我隔着铁窗见他最后一面,他只说‘社稷为重,君为轻’。” “石亨、徐有贞设了天罗地网,就等他反驳。他一辩,守九门的将士、筹粮的百姓、说真话的大臣,全得被安罪名,多少人家要家破人亡?” 这番话落,宪宗攥紧龙椅扶手,指节泛白。他早听宫人提过于谦,此刻才知,于谦是用沉默护住众人的孤臣。 周能的思绪,飘回了正统十四年秋天。 那年七月,瓦剌首领也先南下。明英宗被太监王振撺掇,非要亲征。 吏部尚书王直、兵部侍郎于谦等大臣拼命劝,英宗不听,带着五十万大军出京。 八月十五,土木堡一声炮响,明军精锐尽失,英宗被俘。消息传回北京,朝堂大乱。 侍讲徐珵(后来的徐有贞)喊:“南迁南京才能自保!” 不少大臣附和,孙太后抱着太子哭。 就在这亡国关头,于谦站出来怒斥:“言南迁者可斩!京师是天下根本,忘了南宋的教训吗?” 周能当时在殿外当值,见于谦目光坚定,那声怒吼让朝堂瞬间安静。 后来,于谦劝孙太后立郕王朱祁钰为帝(明代宗),也先 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 的图谋彻底落空。 三天后,于谦任兵部尚书,主持防务。 周能记得,于谦那些日子几乎不睡:白天巡九门,晚上筹军务,烛火常燃到天明。 京城兵力空,他从河南、山东调兵,一月集结二十多万大军;粮草不够,就用 “兵随粮走” 的法子,省民力又防劫粮;为稳军心,他斩了王振党羽马顺,官袍被撕烂也面不改色。 德胜门之战前,于谦部署完兵力,当众立规矩:“军队出城列阵,城门关闭。退后者斩!将帅弃兵者斩!士兵弃将者,后队斩前队!” 他看着周能等人:“我守德胜门,这里是瓦剌主攻方向,愿与诸位共生死。” 那天,于谦穿甲胄立在城门前,身后 “于” 字大旗飘着,虽为文官却自带威严。 战役打响,于谦和副总兵范广设诱敌计:少量骑兵佯装溃败,引瓦剌精锐入埋伏圈。 也先的弟弟孛罗带骑兵闯进来,于谦一声令下,火炮齐鸣、箭矢如雨,瓦剌军大乱。 周能在乱军中砍杀,远远望见于谦站在土坡指挥,流矢擦耳而过也不动。 五天后,也先带着英宗北撤,北京保卫战全胜。 可谁也没料,这大功竟成了催命符。 景泰元年,也先见扣着英宗没好处,提出送他回京。代宗面露难色,于谦劝:“帝位已定,该迎回上皇,有事我担责。” 英宗回京后,被软禁在南宫。周能劝于谦避锋芒,于谦摇头:“我掌兵部,守的是江山,不是某个人的帝位。” 景泰八年正月,代宗病重。石亨、徐有贞、曹吉祥发动 “夺门之变”。 周能那晚巡逻,见石亨撞开南宫大门,扶英宗上龙轿。他连夜去于谦家报信。 可于谦正批军报,听了政变消息只说:“知道了,江山还在就好。” 周能急得跺脚:“他们要清算你,快写辩书啊!” 于谦指《大明律》:“他们要的是我命,辩了没用。” 果然,英宗复位第二天,于谦以 “谋逆” 被捕。徐有贞诬他 “欲立外藩”,石亨说他 “擅权”,于谦始终不说话。 周能和旧部想帮他传辩词,被拒:“我一辩,牵连你们和百姓,宁可我死。” 正月二十二,崇文门外刑场满是百姓。周能被拦在外面,见于谦穿囚服走向断头台,神色坦然。 刽子手刀落,百姓哭着喊 “冤枉”,有人扔馒头咸菜。当晚,刽子手自刎,血书 “杀忠良者不配活”。 几天后锦衣卫抄家,周能跟着去收遗物。可于谦家只有破桌椅和书,唯一 “贵重物” 是代宗赏的蟒袍宝剑,包着没开封。 锦衣卫指挥使叹:“于公清廉,我辈愧煞!” 士兵悄悄放银两在桌上。 “奸臣以为杀了于少保就没事,可天道好还。” 周能拉回宪宗思绪,“石亨下狱饿死,徐有贞贬死云南,曹吉祥谋反被斩。可这些,于少保看不到了。” 宪宗擦了擦泪,拿起案头《明史》草稿:于谦巡抚河南山西十八年,开仓救灾、跳黄河堵口,写 “清风两袖朝天去”,百姓叫他 “于龙图”。 这些话叠在一起,忠臣形象在宪宗心里立起来。 “于少保是真社稷之臣!” 宪宗当即平反:追赠太傅,赐谥 “肃愍”;迁灵柩回杭州,一品安葬;修祠堂供祭拜。 旨意到杭州,百姓沿街跪拜,哭声传数十里。 周能走出暖阁,想起于谦常说的 “但愿苍生俱饱暖”。于谦从不在意功名冤屈,他守的从不是帝王,是天下苍生。这份忠诚,终将照亮历史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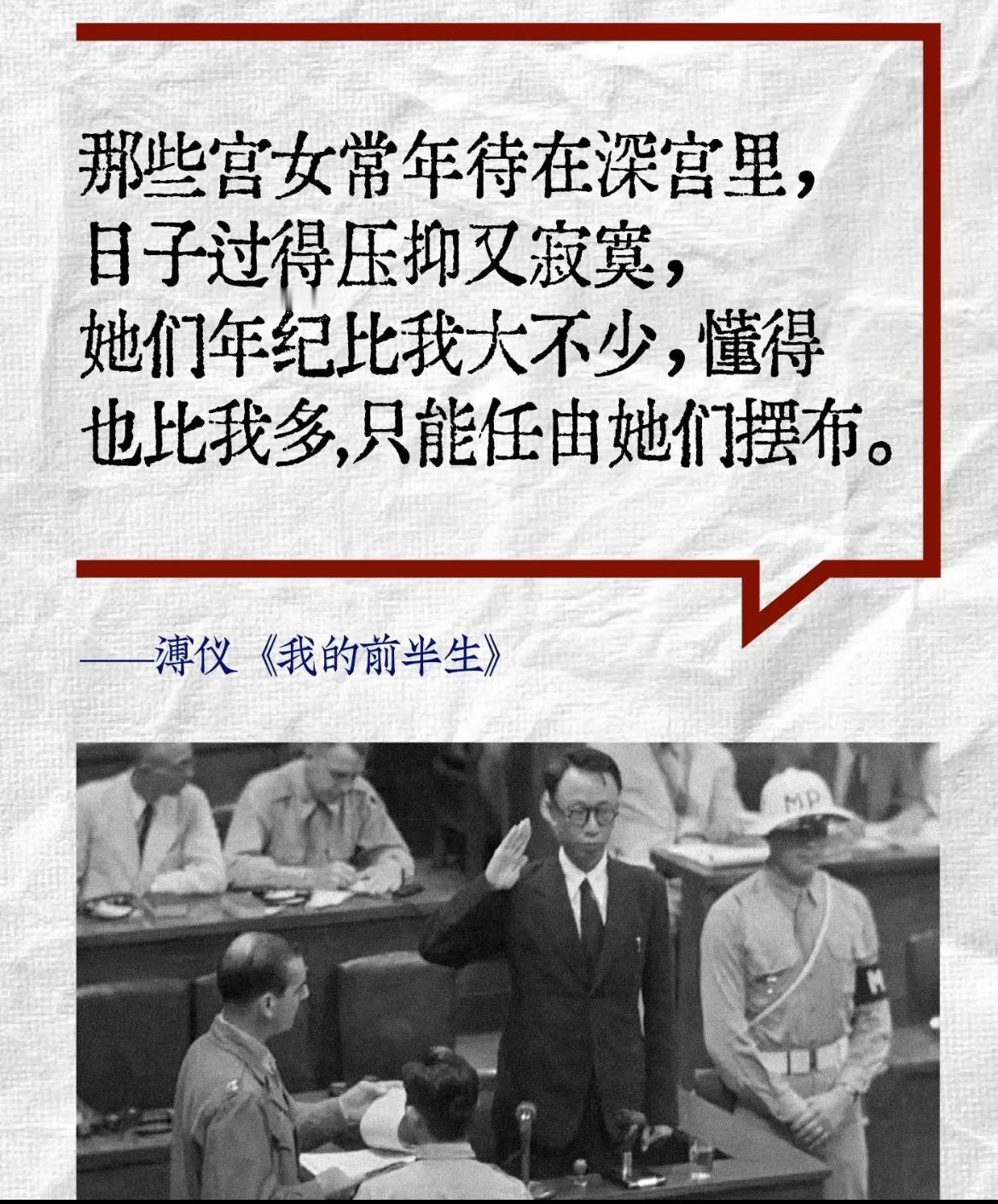

![乾隆真是职业皇帝名不虚传[吃瓜]](http://image.uczzd.cn/5141156089266685545.jpg?id=0)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