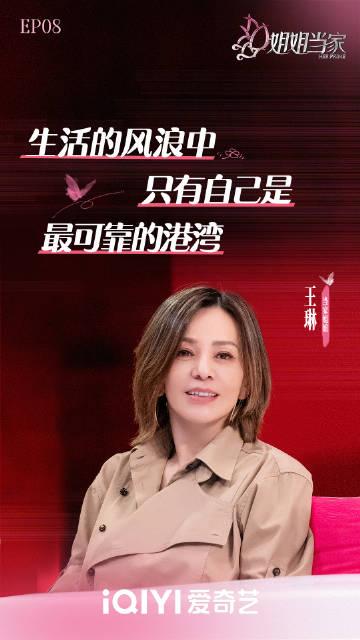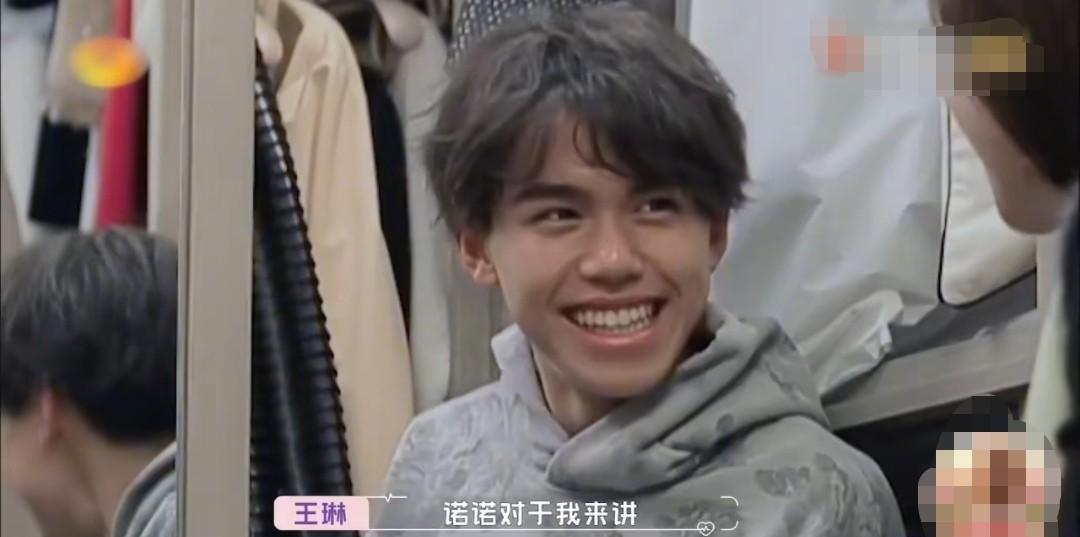王子文建议王琳:“你房子这么大,可以去把父母接回家住。” 王琳直接拒绝:“能给父母安排养老院,就已经仁至义尽了。” 这句利落的回应里,藏着她从七岁到五五岁,横跨近五十年没愈合的原生家庭伤口。 父母是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,却把重男轻女的偏见过成了日常,让她在自己家里活成了 “外人”。 七岁那年,王琳第一次踏进父母在城里的家,迎接她的不是拥抱,而是母亲指着客厅的沙发说:“以后你就睡这儿。” 那时弟弟刚满两岁,有一间带小书桌的卧室,而她的 “床” 是每天要被全家人坐、堆满杂物的旧沙发。 晚上她蜷在沙发角落,能闻到弟弟扔在扶手上的臭袜子味,想挪开却不敢。 前一天她只是把袜子放进洗衣篮,母亲就唠叨了半小时 “女孩子就是事儿多”。 父亲永远坐在书桌前看书,不管家里的争吵,也从没过问她在沙发上睡得舒不舒服。 十三岁,她第一次有了反抗的念头。那天学校要交八十元校服费,母亲给弟弟买了新球鞋,却对她说 “家里钱紧,校服凑活穿旧的”。 她看着弟弟脚上亮闪闪的球鞋,突然问 “为什么弟弟什么都有”,母亲扬手就给了她一巴掌,说 “你是姐姐,让着弟弟天经地义”。 那巴掌打得她耳朵嗡嗡响,她没哭,只是盯着母亲,心里第一次冒出 “要离开这个家” 的想法。 十七岁,她真的开始行动。高考前半年,她每天五点起床背课文,晚上在路灯下刷题,连饭都端着碗在书桌前吃。 有次母亲催她给弟弟洗校服,她头也没抬说 “要复习”,母亲又要动手,她猛地抓住母亲的手腕,嘴角还沾着被打出血的痕迹,却一字一句说 “再打我,我就还手”。 母亲愣住了,那之后没再动过她,却也彻底冷了脸,家里的饭桌上再也没给她留过位置,她只能自己煮泡面吃。 拿到上海戏剧学院录取通知书那天,她没跟家里说,自己收拾了一个小行李箱就走了。 大学四年,她很少回家,寒暑假要么留在学校打工,要么去剧组跑龙套。被选去苏联留学时,她只给家里寄了一张明信片,父母也只回了一句 “注意安全”。 她在国外学会了自己修水管、扛行李,生病时一个人去医院,慢慢习惯了不依赖别人,毕竟从小到大都没人可依赖。 二十五岁,她第一次结婚。对方是比她大三十岁的港商,见了三次面就求婚了。 身边人都劝她想清楚,她却觉得对方说话温和,会给她夹菜,像极了她想象中父亲该有的样子。 可结婚后才发现,两人根本没有共同语言,他不懂她拍戏的辛苦,她也不理解他商场上的算计。 一年后离婚,她没哭,只是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上,很快凭一部剧火了起来。 三十岁,她第二次结婚。这次的丈夫是同行,懂她的职业,也心疼她的过去。 她以为终于能有个家了,可随着儿子出生,两人在育儿观念上的分歧越来越大,最终还是分开了。 这次离婚让她消沉了很久,直到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,她才重新振作,她发誓要给儿子全部的爱,绝不让他像自己一样长大。 这些年,她把儿子带在身边,拍戏时也尽量带着,儿子的家长会、生日会从没缺席过。 儿子上大学后,家里空了下来,她才想起父母年纪大了,于是给他们找了最好的养老院,每月按时打钱,每周去看一次。 可每次见面都很尴尬,母亲只会问 “弟弟最近怎么样”,从没过问她累不累、身体好不好。 有次她感冒发烧,想让母亲来家里陪一天,母亲却说 “我还要给你弟弟带孩子,走不开”。 现在她五五岁了,房子很大,有很多空房间,可她从没想过接父母来住。 不是狠心,是真的不知道怎么相处,她试着跟母亲聊小时候的事,母亲只会说 “都过去这么久了还提它干嘛”;她想给母亲买新衣服,母亲却说 “你弟弟说这个牌子不好”。 她终于明白,有些伤口不是时间能愈合的,有些关系也不是努力就能修复的。 给父母安排好养老院,按时看望,尽到赡养的责任,对她来说已经是极限了。 信源:《姐姐当家》 王琳自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