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时期,有一天,一个老人对儿子说道:“孩子,我看上了咱家十七岁的侍女,我想纳她为妾,你看如何?”听到这里,儿子顿时一紧张,说道:“让我考虑考虑吧。” 乾隆那时候,江南有个刘知府,他老爹七十多岁了还爱玩,家里已经有十个小老婆了。这不,最近家里来了个十七岁的小姑娘小莲,长得水灵灵的,脾气还好,是因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才来刘府打工的。刘知府原本也想把小莲收入后宫,但怕影响官声,就先让她照顾老爹。结果这老爹一看小莲,眼睛就直了,直接跟儿子说:“儿子啊,爹看上咱家那小莲了,想让她给爹当小老婆,你觉得咋样?” 先把这几个人拎出来说道说道。 刘知府,四十出头,脑门上留着两撇油亮的胡子,看着像个清官,实则算盘打得比谁都精。在江南任上捞了不少好处,却总爱穿件洗得发白的官服,见人就念叨“百姓不易”。他对小莲动心不是一天两天了,那姑娘端茶时手腕的弧度,扫地时垂着的眼睫,都让他心里发痒,只是顾忌着“父母官”的名声,没敢动手。 刘老太爷,七十有三,年轻时也是个纨绔子弟,老了更没规矩。家里的十个小妾,最大的三十出头,最小的比小莲还小两岁。他不稀罕金银,就喜欢看年轻姑娘围着他转,觉得这样才能证明自己还没老。 小莲,家住城郊的茅草屋,爹瘫在床,弟弟还在吃奶,她是被娘含泪送进刘府的。进府时穿了件打满补丁的蓝布衫,却掩不住眉眼间的清亮。她话少,干活却麻利,给老太爷捶背时轻重刚好,倒茶时总能端到最舒服的温度,府里的老妈子都说这姑娘“懂事得让人心疼”。 刘知府回了自己的书房,把茶杯往桌上一墩,茶水溅出老高。 他不是不想满足老爹,只是这事儿太膈应——自己惦记的人,被老爹先开口了。更怕的是传出去,人家会说“刘家父子共用一女”,这唾沫星子能把他的乌纱帽淹了。 可老爹的脾气他知道,认定的事八头牛都拉不回。前两年老太爷想要个唱曲儿的戏子,他没答应,老爷子愣是绝食三天,最后还是他花钱买了人送进府才作罢。 正烦着,管家敲门进来:“老爷,老太爷在院里发脾气呢,说您要是不点头,他就搬到庙里去住。” 刘知府捏着眉心,突然问:“小莲最近跟谁走得近?” 管家想了想:“就跟后厨的春桃说过几句话,都是些家里的苦处。” 第二天一早,刘知府去了老太爷的院子,脸上堆着笑:“爹,您想要小莲,儿子哪能不依?只是这姑娘刚进府,不懂规矩,得先调教调教,过两个月再给您办喜事,风风光光的,您看咋样?” 老太爷一听乐了,胡子都翘起来了:“还是我儿子懂爹!” 刘知府转身就叫来了小莲,把她领到一间空房,房里摆着个红木箱子。他打开箱子,里面是几件花布衣裳,还有一锭十两重的银子。 “小莲,”他语气放缓,“你也知道老太爷的心思,只是他年纪大了,怕是……”他故意顿了顿,“你要是不愿意,拿着这些银子,我派人送你出城,给你爹请最好的大夫,再给你弟弟找个学堂。” 小莲的手猛地攥紧了衣角,指节发白。她抬头看了看刘知府,又低头看了看银子,眼泪“吧嗒”掉在地上。 她没说愿意,也没说不愿意,只是对着刘知府磕了个头,拿起那锭银子,转身走了。 刘知府看着她的背影,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,说不上是松快还是憋屈。 当天下午,小莲就跟着管家出了府。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,只听说城郊的茅草屋前,来了个郎中,还搬来了两袋米。 过了两个月,刘老太爷见小莲没回来,又开始闹。刘知府没办法,从苏州买了个会弹琵琶的姑娘送进府,老太爷见这姑娘比小莲更会哄人,渐渐就把小莲忘了。 刘知府还是天天穿着那件发白的官服,审案子,收赋税,只是偶尔路过城郊,会让轿子停下,往茅草屋的方向望两眼。 有回他微服私访,在镇上的杂货铺门口,看见个抱着孩子的妇人,正给一个瘫子喂药。那妇人穿着干净的粗布裙,眉眼间还是那么清亮,只是眼角多了点细纹。 是小莲。 她也看见了他,愣了愣,抱着孩子往旁边躲了躲,低着头没说话。 刘知府的脚步像被钉住了,看着她给丈夫擦嘴角,给孩子换尿布,动作熟练又温柔。阳光照在她脸上,没有了在府里的怯懦,多了种踏实的暖意。 他没上前,转身默默离开了。 后来有人跟他说,小莲用那十两银子给爹治了病,还嫁给了邻村一个老实的木匠,木匠虽然腿有点瘸,却把她当宝贝疼。 刘知府听了,没说话,只是那天晚上,他喝了不少酒,对着空杯子笑了笑,又叹了口气。 这事儿说起来,刘知府算不上好人,他对小莲的“成全”,说到底还是为了自己的名声。可比起那些强抢民女的官老爷,他终究是给了小莲一个选择。 小莲也不是什么烈女子,她拿了银子,选了条能让家人活下去的路。可在那个年月,一个底层女子,能靠着自己的隐忍和运气,换得一份安稳的日子,已经算是难得的结局了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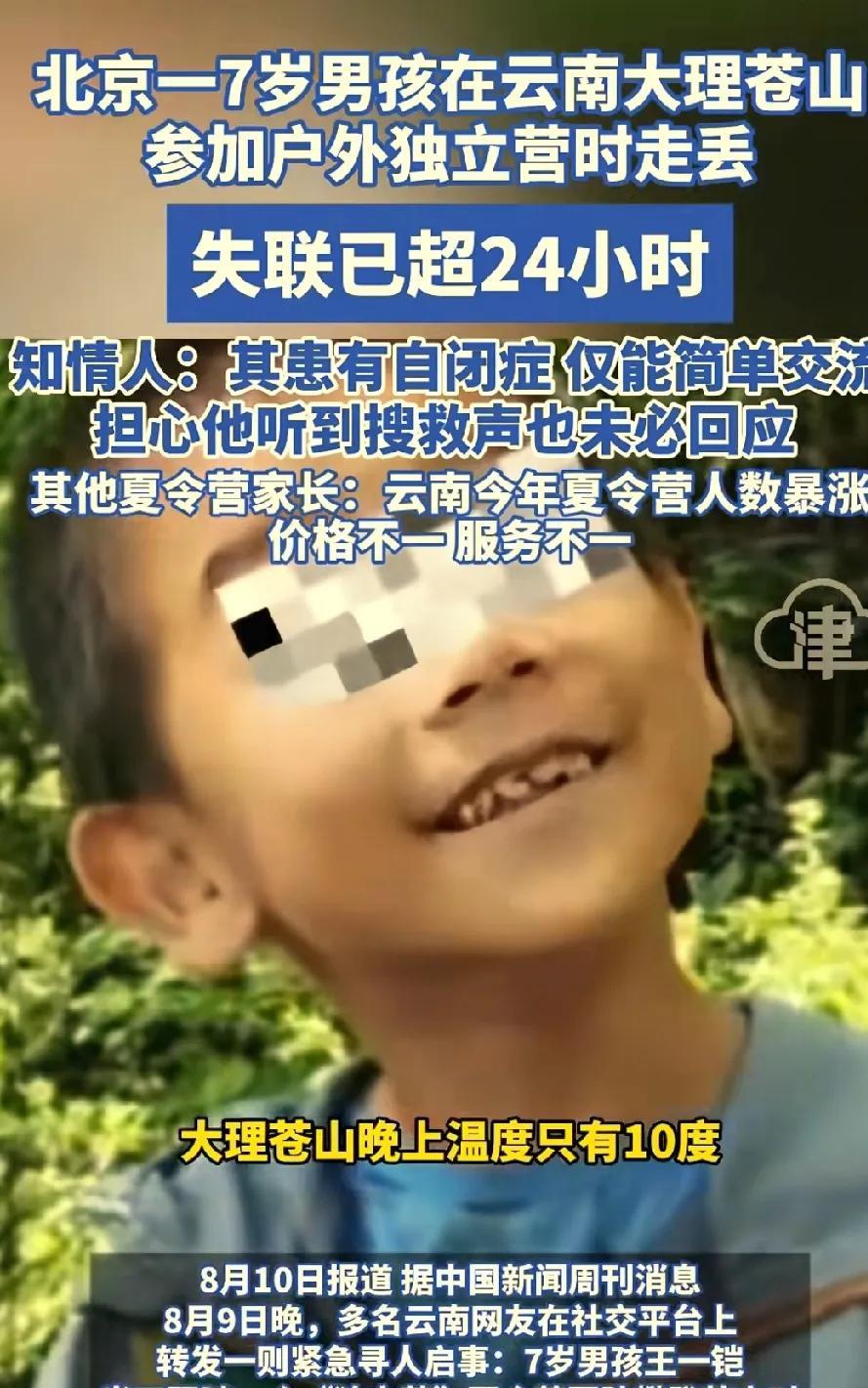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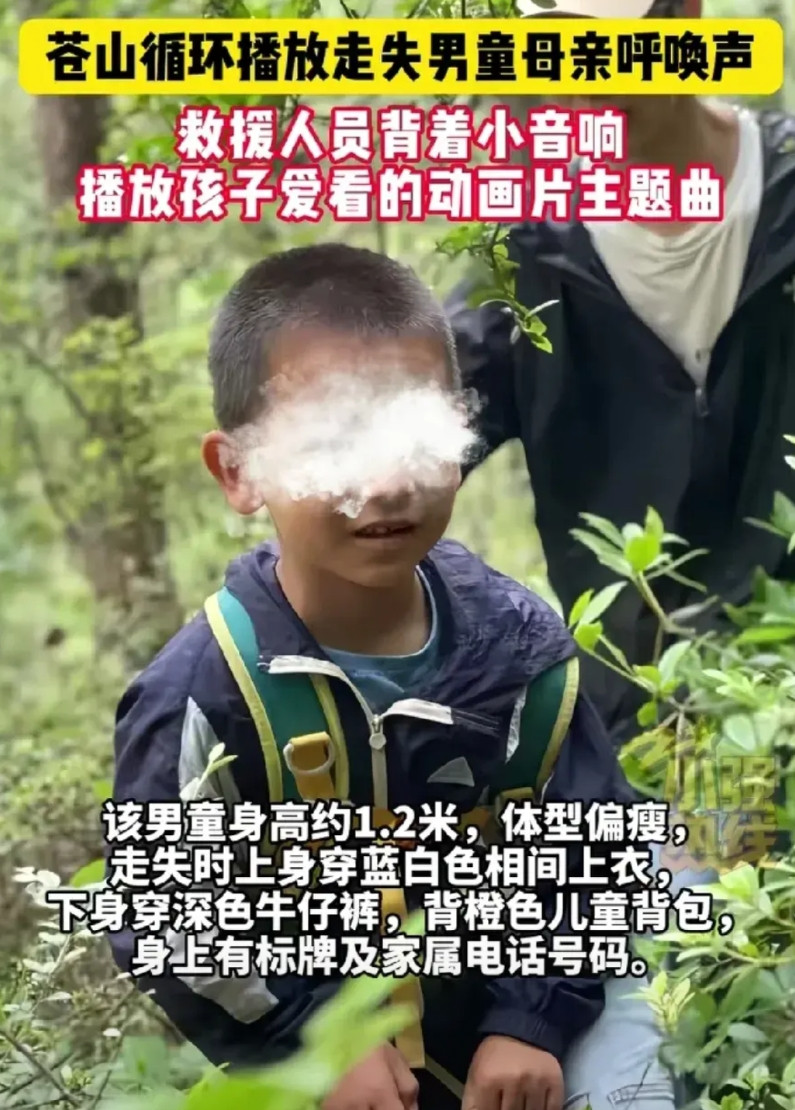

![65年的年入12万要找20岁的小姑娘生孩子?[惊恐]](http://image.uczzd.cn/1258478805856979202.jpg?id=0)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