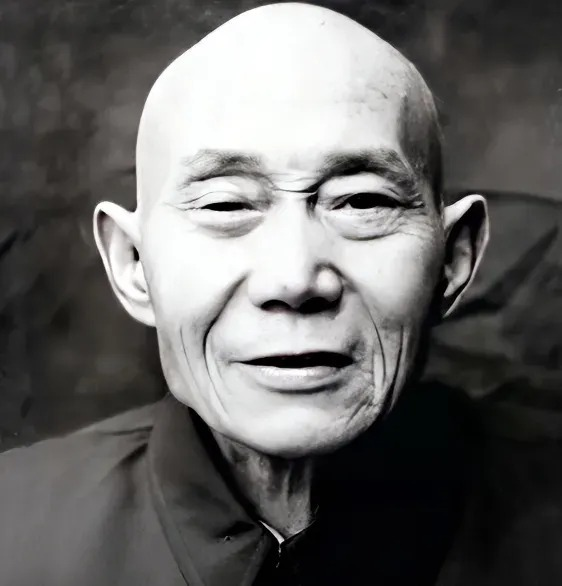1938年夏,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、邓华挺进冀东,与冀东起义武装主力会合,这引起了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震惊。由于冀东是联结东北和华北的咽喉地带,直接威胁着平津等地的安全。为此,日军大本营有感华北方面军兵力不足,急从国内抽调第110师团于7月进入平津地区。在山下奉文等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长官的部署指挥下,第110师团与关东军相配合于8月份对冀东进行了大规模“讨伐”和围追堵截,迫使八路军第四纵队主力和冀东武装大部于10月向平西转移,10万暴动武装在转移中大部失散。 时至1939年,鉴于华北占领区内八路军发展的迅猛,为了实现大本营的意图,即“确保占领地区,促使其安定,以坚强的长期围攻的阵势,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”,华北方面军总参谋长山下奉文等在杉山元总司令官(1938年11月25日接寺内寿一职)的要求下,主持拟定了《1939年度治安肃正纲要》。 作为华北方面军的总参谋长,山下奉文时刻关注着各地肃正作战的进度。尽管各地作战击溃了一些国民党残余武装,但是面对实施游击战术的八路军,日军却战果不佳,并屡遭打击。这对于山下奉文来说,不能不产生一些压力和不利途仕的影响。应当指出的是,正是山下奉文指挥进行的这些所谓“围剿”、“治安”战等,制造了大量血案,在广大华北地区犯下了滔天罪行。 在积极实施治安肃正战的同时,山下奉文等还积极关注着整个中日战争的全局。他通过思考提出,“中国排除英国势力是对华政策之根本”。山下奉文后来任第25军司令官指挥马来作战时,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记载:“中国问题的解决除以中国人民的独立为根本而进行中日提携之外,别无他途。”由于山下奉文积极主张实行“中日提携”,对英法在华势力的存在极为不满,所以他对日本内阁中的一些“稳妥”政策表示出相当的不同意见。1939年6月14日,山下奉文在副参谋长武藤章的协助下,不顾来自陆军省的劝阻,下令封锁天津英法租界。由于英法等国正积极谋划“东方慕尼黑”,因此并没有对山下奉文所实施的行为采取过激反应。倒是日本政府利用这一事件不断给英法施加压力。最终,英日双方于7月24日签署了《有田—克莱琪协定》,规定:英国“完全承认”日本造成的“中国之实际局势”;承认日本在其占领区内享有“特殊之要求”;允诺“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动与因素”,英国“均无意加以赞助”。 尽管封锁租界事件给日本政府在对英法外交上获得了取利的机会,但却并没有给山下奉文捞取太多的好处。9月中旬,日苏诺门坎事件以日本的失败告终。作为善后的处理,关东军的首脑和作战参谋等均被撤换。9月23日,山下奉文调离华北方面军,出任关东军第四师团长,隶属关东军司令官是梅津美治郎之下。在这期间,山下奉文原有意被酝酿出任驻蒙军总司令,可是却意外地调赴东北,使其前途又被蒙上一层阴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