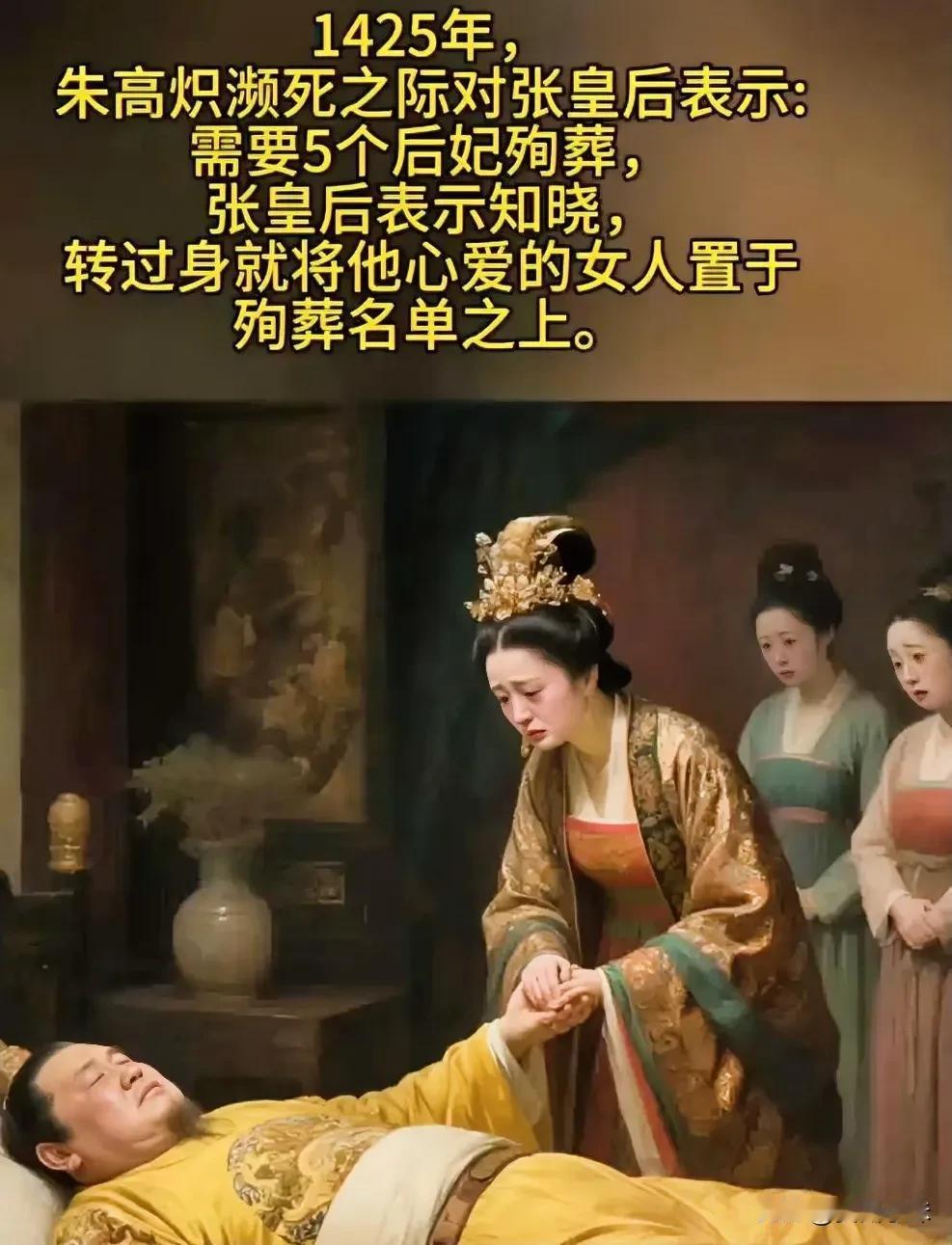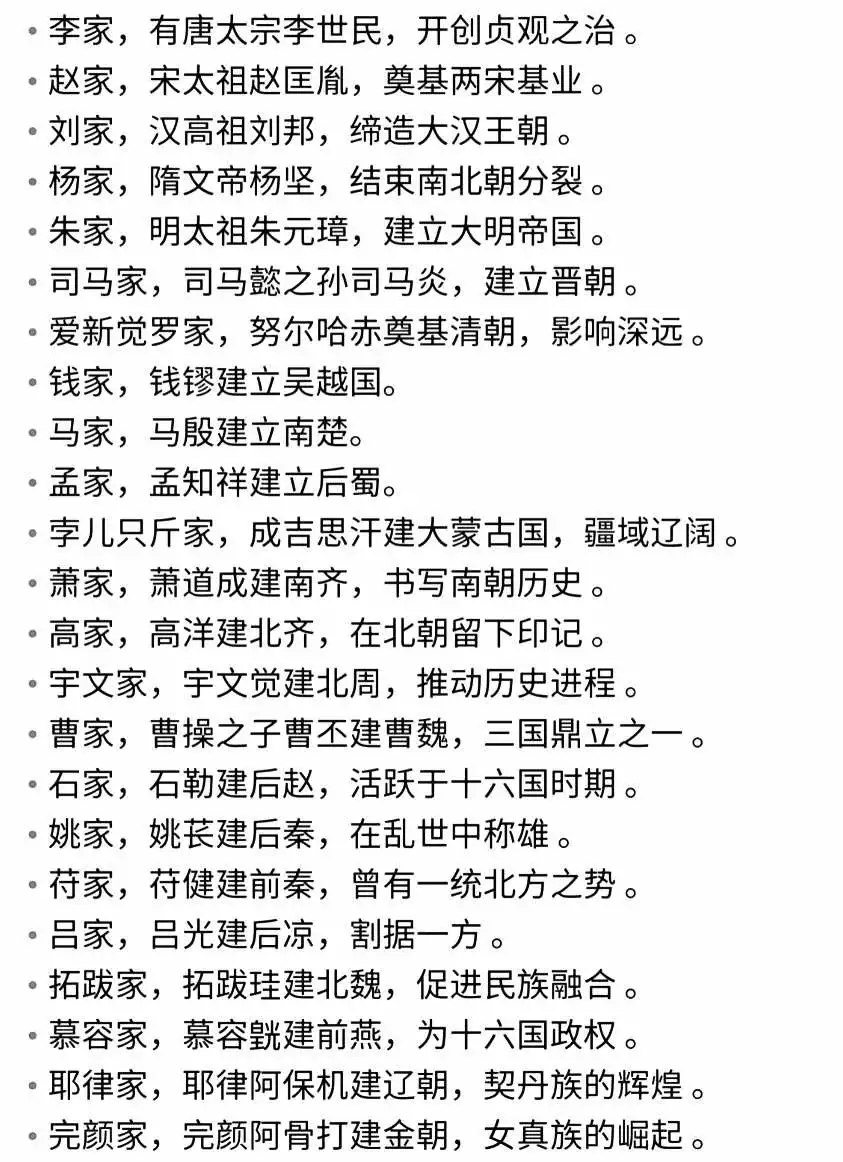1461年5月,弋阳王朱奠壏和母亲白太妃被押赴法场,罪名是通奸。这场皇室大案的背后,却是因一袋黄金,所引发的诬告。 要讲清这场冤案,得先从弋阳王朱奠壏的皇室血脉说起。朱奠壏的祖父是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,就是那位手握重兵、封地在大宁的宁王。 洪武年间的宁王朱权可不是等闲之辈,不仅文采斐然,更能带兵打仗,是明初藩王中的佼佼者。 靖难之役时,朱棣用计胁迫朱权加入 “清君侧” 的阵营,承诺事成之后 “天下中分”。可等到朱棣登基后,当初的诺言早已抛到九霄云外。宁王不仅没分到半壁江山,反而被改封到南昌。之后,这位郁郁不得志的王爷只能寄情于文学戏曲,在江南水乡消磨余生。 朱权死后,长子朱磐烒袭爵为宁王,朱奠壏是朱磐烒的庶子。按照明朝 “嫡长子继承制” 的规矩,庶出的朱奠壏无缘宁王爵位,最终在正统四年(1439 年)被封为弋阳王。 弋阳王府虽不如宁王本府风光,却也衣食无忧。朱奠壏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,在宗室中口碑尚可。他的母亲白太妃是朱磐烒的侧妃,在丈夫去世后,作为王太妃在府中安享晚年。 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,这对母子本该在南昌的王府中过着平静的贵族生活,可命运的齿轮却因一袋黄金悄然转向。 正统年间的南昌城里,弋阳王府与当地官府往来频繁。王府的日常用度、修缮维护都需要与地方官员打交道,而这其中难免产生利益纠葛。 天顺三年(1459 年),一场看似普通的黄金交易,成了引爆这场冤案的导火索。 当时弋阳王府要修缮宫殿,需要一批成色上好的黄金装饰梁柱。王府内使阮敬奉命与南昌府的官吏 接洽采买事宜。按照约定,王府支付了足额的银两,却迟迟没收到合格的黄金。 几番催促下,地方官才送来一批成色不足的黄金,重量也短少了不少。朱奠壏得知后十分恼怒,当着众人的面斥责了阮敬办事不力,还扣了他当月的俸禄。 这本是王府内部的管理问题,却让阮敬怀恨在心。这位在王府服役多年的内使,平日里仗着王爷的威势在地方上作威作福,如今当众受辱,觉得颜面尽失。更让他不安的是,他在采买过程中暗中克扣了,本想蒙混过关,如今黄金出了问题,生怕事情败露会受到更重的惩罚。 思来想去,阮敬决定先下手为强。 阮敬联络与自己素有交情的王府典宝栾真,两人一拍即合,决定编织一张足以将弋阳王母子置于死地的大网。 天顺四年(1460 年)冬,一封署名阮敬、栾真的密奏通过锦衣卫的渠道送到了明英宗朱祁镇的御案上。 奏疏中言辞凿凿地指控弋阳王朱奠壏 “素行不端,与母白太妃私通有年”,还列举了所谓的 “证人” 和 “证据”,甚至编造了王府内侍深夜目睹 “秽乱之事” 的细节。 明英宗看到奏疏时的震惊可想而知,这位经历过土木堡之变、夺门之变的帝王,对皇室丑闻有着天然的敏感。 此外,弋阳王作为宁王后裔,祖上朱权与成祖朱棣的恩怨早已是公开的秘密,这让英宗对这一脉宗室本就多了几分猜忌。 英宗下令由锦衣卫指挥逯杲负责彻查此案, 逯杲以心狠手辣、罗织罪名闻名,在查办案件时向来不择手段。让这样的人负责此案,就注定了朱奠壏的悲剧结局。 锦衣卫的校尉们如同饿狼般扑向弋阳王府,朱奠壏和白太妃被迅速软禁,王府上下被翻了个底朝天,“证人” 们被带到锦衣卫诏狱。 被抓来的王府内侍大都胆小怕事,在锦衣卫的威逼利诱下,很快就按照阮敬事先编造的 “剧本” 招供了。有人 “承认” 曾看到弋阳王深夜进入白太妃寝宫,有人 “证实” 母子二人用餐时举止亲昵,甚至还有人 “回忆起” 多年前似是而非的 “异常情况”。 负责主审的逯杲添油加醋地写成结案报告呈给英宗,英宗看完后勃然大怒,他没有考虑案件中的诸多疑点,当即拍板:“弋阳王母子秽乱宫闱,罪不容诛,着即问斩。” 法场悲歌与惊天反转 1461年 5月,朱奠壏和白太妃在南昌被处斩。就在两人人头落地的三个月后,事情突然发生了惊天反转。锦衣卫在查办另一起案件时,意外抓获了阮敬的同党栾真。 在审讯中,栾真为了活命,竟然全盘招供了与阮敬合谋诬告弋阳王的全过程。他不仅交代了黄金纠纷的来龙去脉,还供出了如何买通证人、如何编造供词的细节,甚至拿出了阮敬给他的封口银两作为证据。 案情真相大白,锦衣卫立刻将此事上报英宗。当英宗看到栾真的供词时,整个人都僵住了。他这才意识到,自己一时冲动竟然错杀了皇室宗亲,还是以如此屈辱的方式。 英宗下令将阮敬凌迟处死,抄没家产,所有参与诬告的人都被严惩。 可人死不能复生,弋阳王母子的冤屈虽然得以昭雪,却再也换不回他们的性命。英宗内心充满愧疚,他下旨为朱奠壏恢复名誉,追复弋阳王爵位,并按照亲王礼制重新安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