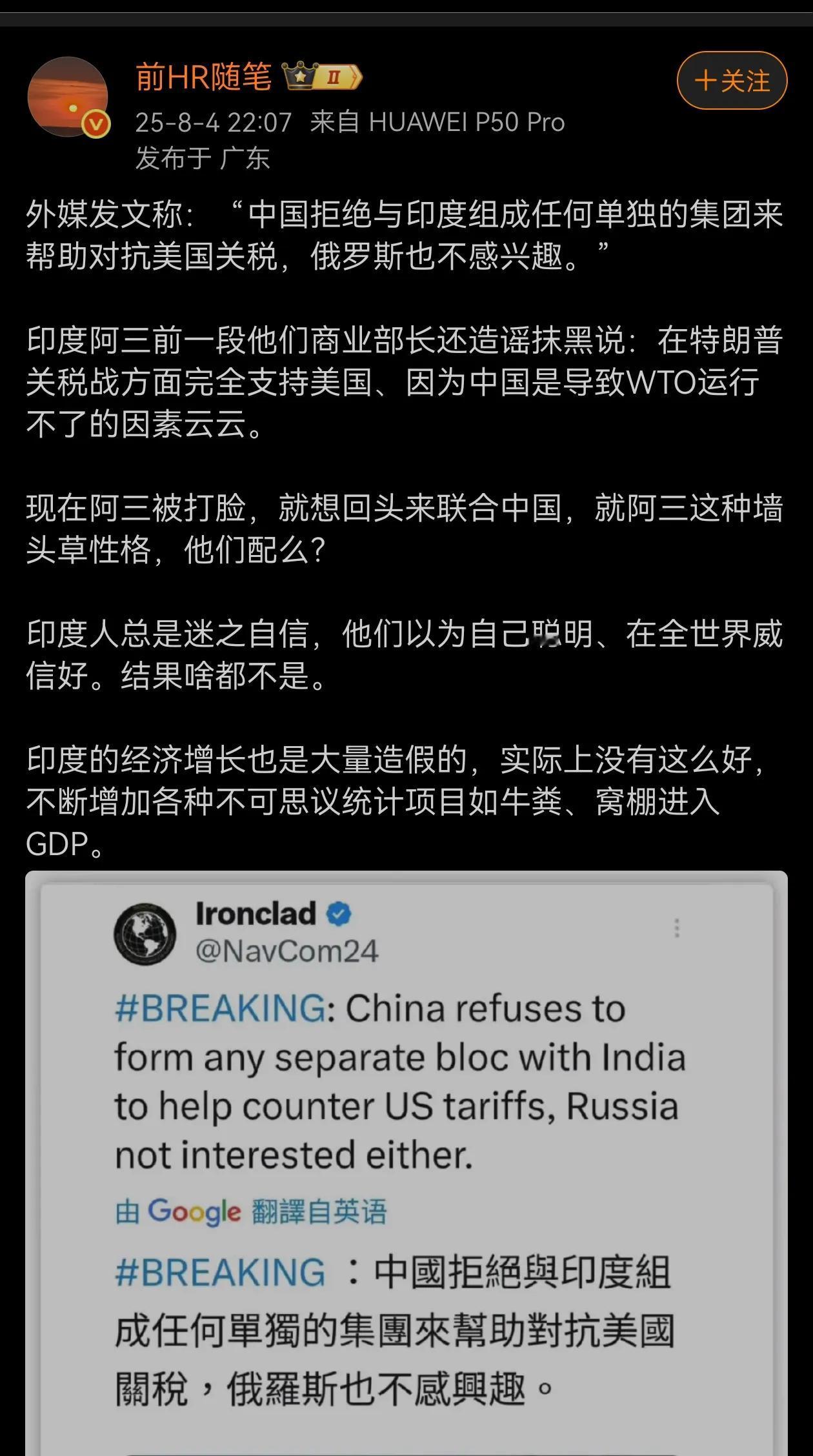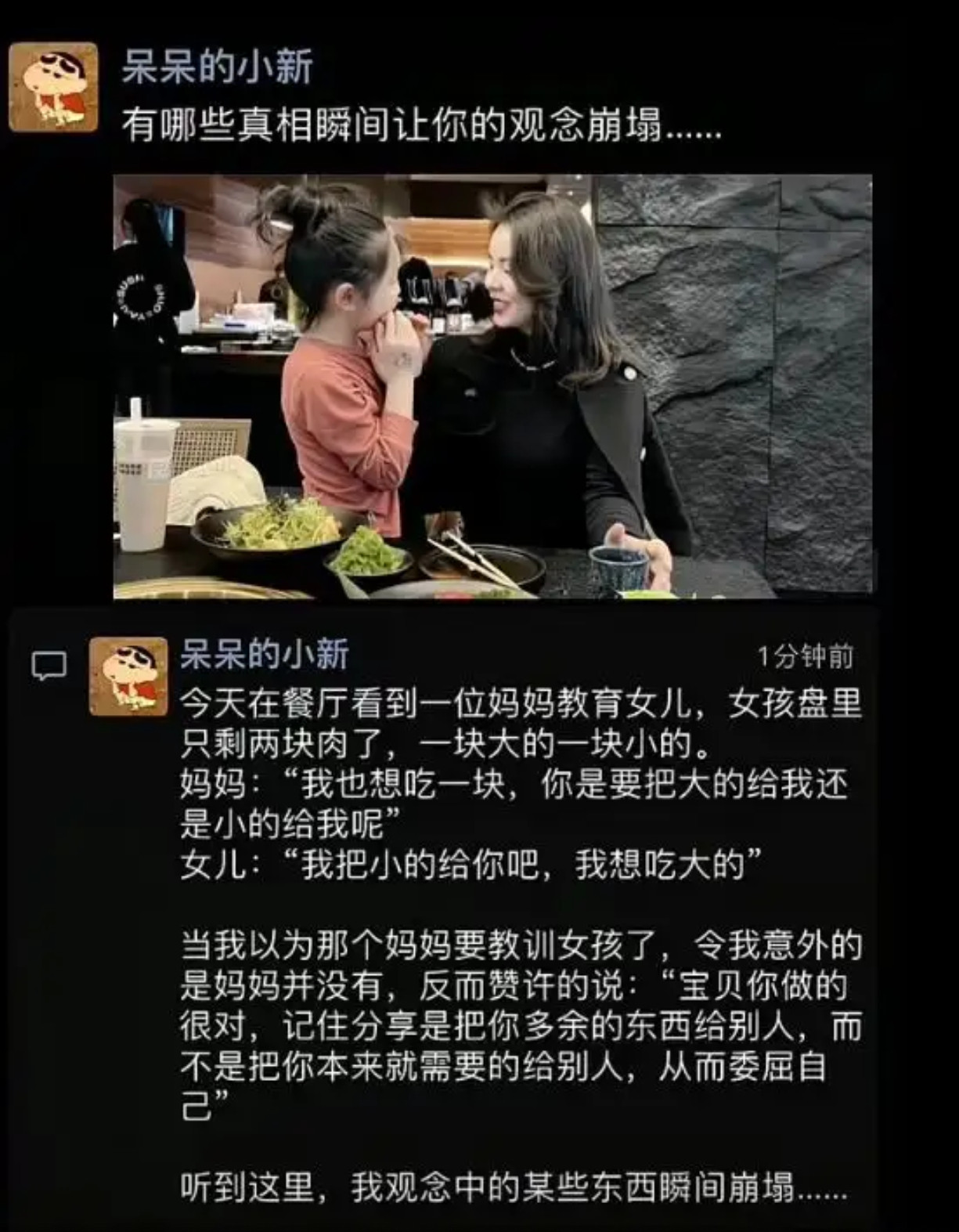从许倬云的“晚节”说起
几个月前对岸的明教授在一期访谈节目上拷问蓝(大意):你们父祖当年拖家带口,背井离乡,播迁外岛,为的是什么,为的不就是逃避康米主义,寻找自由吗?!现在那边强大了,你们不辨表象背后公平正义是否有亏,轻易抛弃来之不易的制度,投怀送抱,忘记初心,这么做对得起父祖吗?!
说当年那代外省人逃避康米主义不假,但是不是追寻民主却大有疑问,毕竟现实是他们接下来生活在近四十年的戒严之下,很多人甚至没有亲眼见到“解严”的那天。当年迁台的这群人,特别是学界和政经界人士,除了担忧即时的政治清算,对康米主义有两大远期疑虑,一是经济上过于乌托邦,令国家陷入贫困,二是文化上过于激进,破坏传统毁灭文脉。众所周知,这两大疑虑皆得到历史的阶段性证明。而后,东大改弦更张,借全球资本主义产业转移的机遇,在“四小龙”之后也走上重振之路,由于两岸在土地和人口上的巨大差距,东大后来居上、综合国力逐渐甩开对方当然也是不难预料的。在经济改善的同时,东大的文化政策亦发生转向,无论背后的政治考量,对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,表现出亡羊补牢的决心。当年逃避康米主义的两大疑虑既消,外省人和他们的后代在地域认同和文化基因的双重作用下,大部分人在九十年代以来日益心向东大,是理之固然。至于明教授批评他们不珍惜本岛制度文明,虽闻之警醒,但终究是没摸到这代人的心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