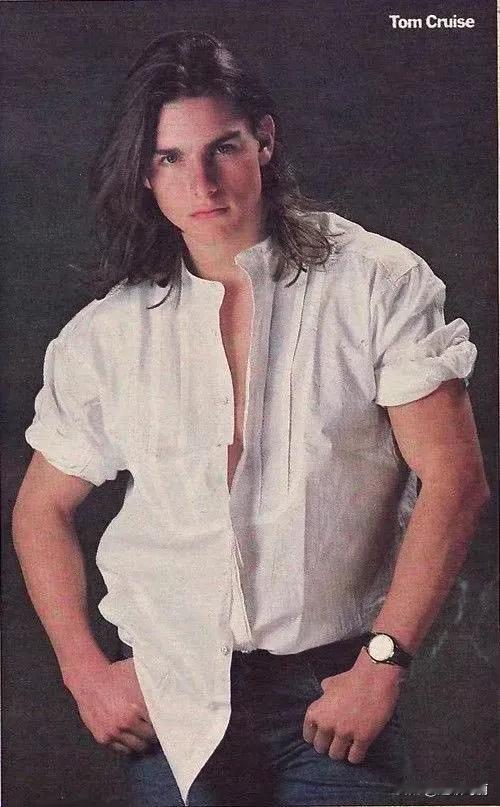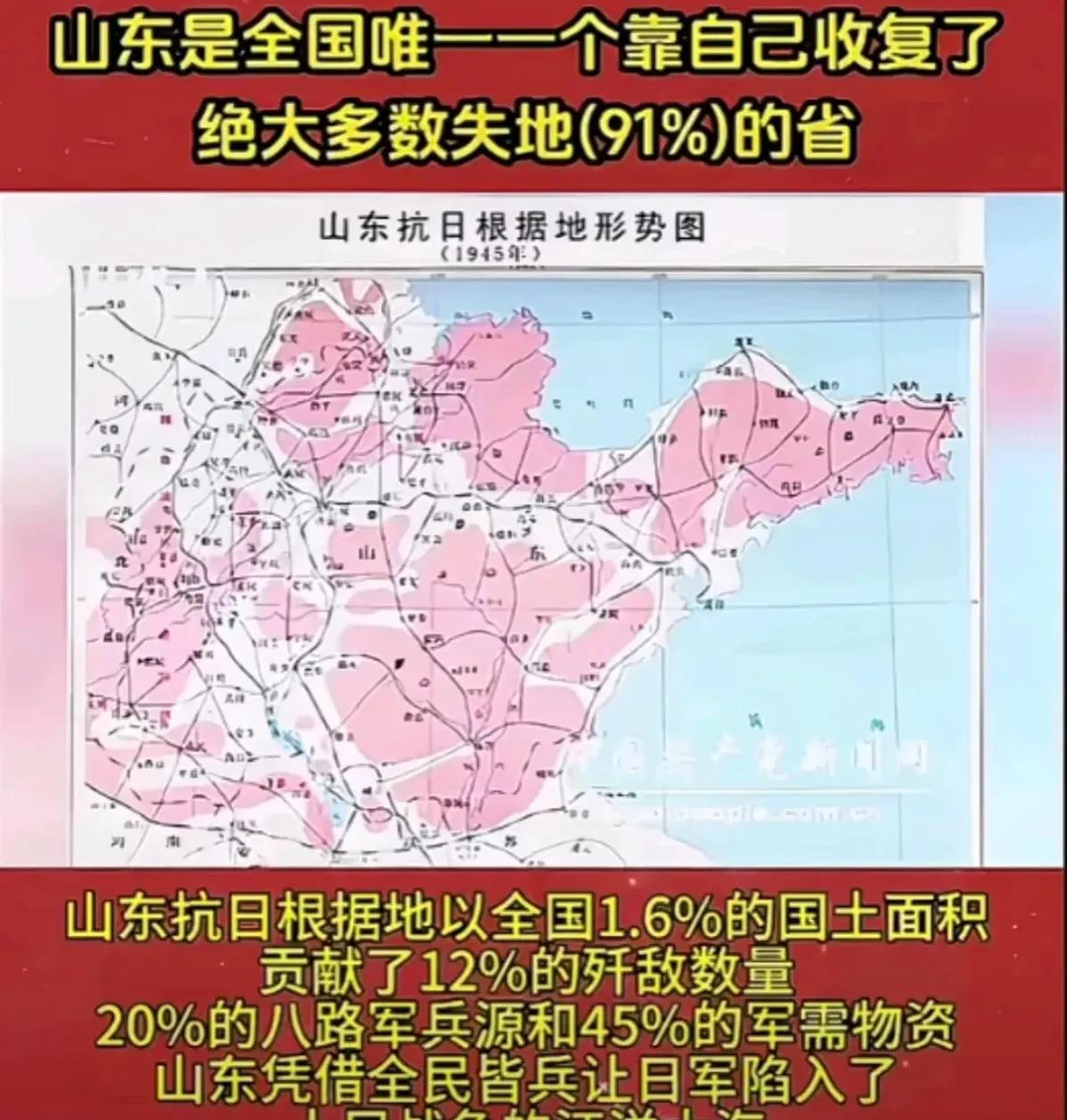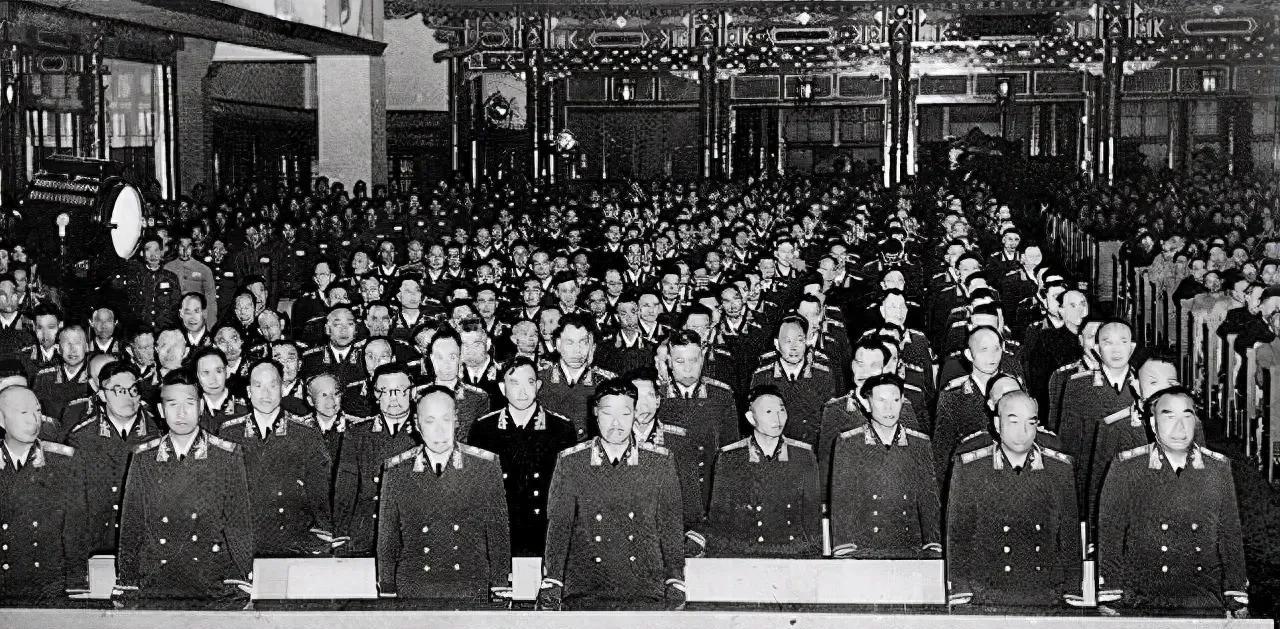沈醉对改嫁的前妻念念不忘,相见后释怀,现任妻子:这下死心了吗 “1979年3月的一天,我想去香港看看她。”沈醉的声音很轻,却像在审判自己。坐在旁边的女儿沈美娟愣了几秒,只回了一句:“爸,您早该去了。” 这一幕,从侧面勾勒出沈醉战后三十年的隐痛。外人总记得那位握着双枪、审讯江姐的军统少将,却容易忽略,被关进功德林后,他夜里反复梦到的只有“雪雪”二字。对一个曾经自诩冷血的大特务而言,这份执念几乎比牢饭更难咽。 时间拨回1932年。那年上海“一·二八”炮火尚未散尽,十八岁的沈醉因在长沙组织抗日示威,被学校除名。失学的灰暗,让他轻易抓住姐夫余乐醒伸来的那只手。余是复兴社上海区区长,手下缺个交通联络员,聪明又能吃苦的沈醉就这样闯进了戴笠视线。 短短六年,他靠面冷心狠的办事风格升到军统总务处处长。暗杀宋庆龄未遂,使出“车祸伪装”这一招虽然没得手,却让戴笠看见他“敢赌命”的优点。此后绑架、渗透、反间……他在国民党内部几乎无所不能。 就在这一条血色上升通道上,他遇见了学员粟燕萍。常德特训班的泳池边,姑娘为打破僵局跳入深水,随即呛得直沉。沈醉下意识跃入水中,把她拖上岸。在军统课堂上拿惯决策刀子的男人,这回只会笨拙地拍着对方背部。18岁女孩眼里,那一碰便成了依靠。 回长沙省亲的路上,两人把各自的苦处越聊越透。粟父病榻前误把沈醉当准女婿,让这段暧昧瞬间坐实。戴笠原立规矩禁师生恋,却也对沈醉网开一面——功课做得漂亮的人,总能得到额外豁免。于是那句“雪雪”成了沈醉之后十一年颠沛生活里最温暖的称呼。她给他生了六个孩子,他则请保姆、揽家务,只求家人随他天涯流离。 1949年底,昆明风云突变。郑介民、毛人凤已远遁台湾,唯独沈醉被留在原地断尾。卢汉举义在即,他来不及多想,只将妻儿送上飞往香港的班机,自己继续周旋。12月,城市天平终于倒向解放军,他签下起义电文,随即移交军管会。接着便是功德林十一年劳改。 新政下的功德林不再简单锁人,斗争、学习、写家书全部排上日程。沈醉翻旧毛衣练针脚,一针一线写“雪雪”名字,改造纪录里几乎每三页就出现她。他以为坚持几年便能团聚,没料到1960年特赦时只收到一封语气疏离的来信——没有地址,没有近况,只附上一张合影。她身边站着一个陌生军官。 好友暗中查到真相:粟燕萍早年投资失利,带着孩子捱不过窘困,只得与滞留港岛的唐如山搭伙。更揪心的是,五个孩子被毛人凤以“忠烈遗孤”名义强行接走去台湾。听完这些,沈醉沉默到脸色发青,却没再像从前那样掏枪找仇人。他只在日记里写了八个字:“无可奈何,生计使然。” 政协干部看他日渐消瘦,几次劝再成家。40岁的护士杜雪洁被介绍来相亲,她的姓里同样有个“雪”字,这细节让沈醉动摇。第一次见面他递上一封长信,把自己的过去摊得干干净净。杜雪洁读完只是笑,说:“我看重的是现在的你。”两个月后他们补办完离婚手续,正式登记。有人打趣:“大魔头变新郎,够戏剧。”沈醉苦笑:哪有什么戏剧,不过是活下去的另一种姿势。 进入八十年代,起义将领身份落实,副部级待遇随之而来。往昔罪行仍要反思,但生活确实宽裕了。香港与大陆通邮日益便捷,他终于鼓起勇气踏上那趟飞机。同行的只有小女沈美娟,既作见证,也帮父亲壮胆。 铜锣湾的老公寓里,61岁的粟燕萍白发稀疏,早无昔日风华。唐如山站在一旁,略显局促。沈醉看了看他们,率先伸手:“沈某当年负你们母子,今日惟有道歉。”唐如山愣住,片刻后回握:“孩子们能平安长大,都是幸事。”短短几句话,把三十年纠结拆得七零八落。 离开公寓时,夜色浓重。杜雪洁的电话正好打进来,她半真半假问:“这下死心了吗?”沈醉倚在港湾栏杆,只回了两个字:“放心。”声音不高,却足以盖过海风。 历史书上写不完的,是沈醉前半生的血与火;写得完的,是一个晚年男人把锋芒磨成钝器后,对家人、对旧人交出的答案。昔日特务、今日老人,再回头,枪声已成旧档案,唯一还能握在手里的,只剩下如何善待余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