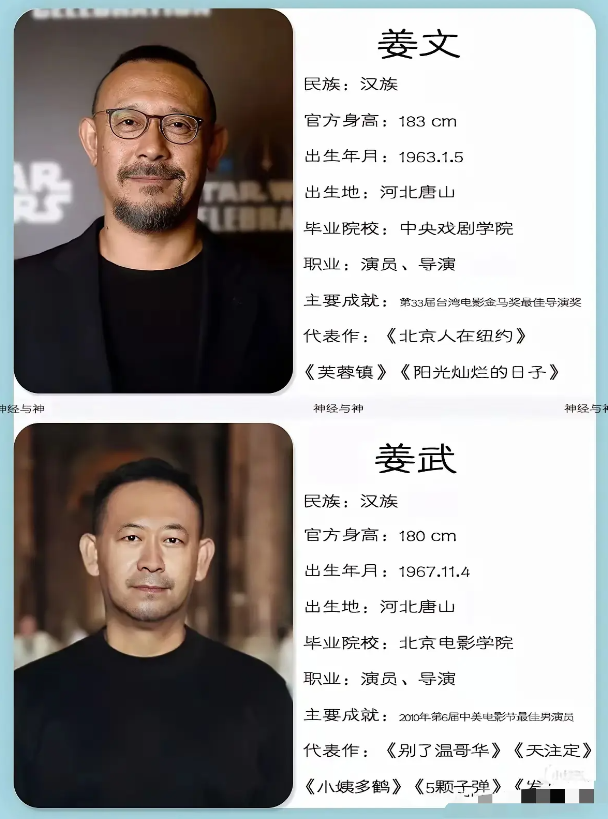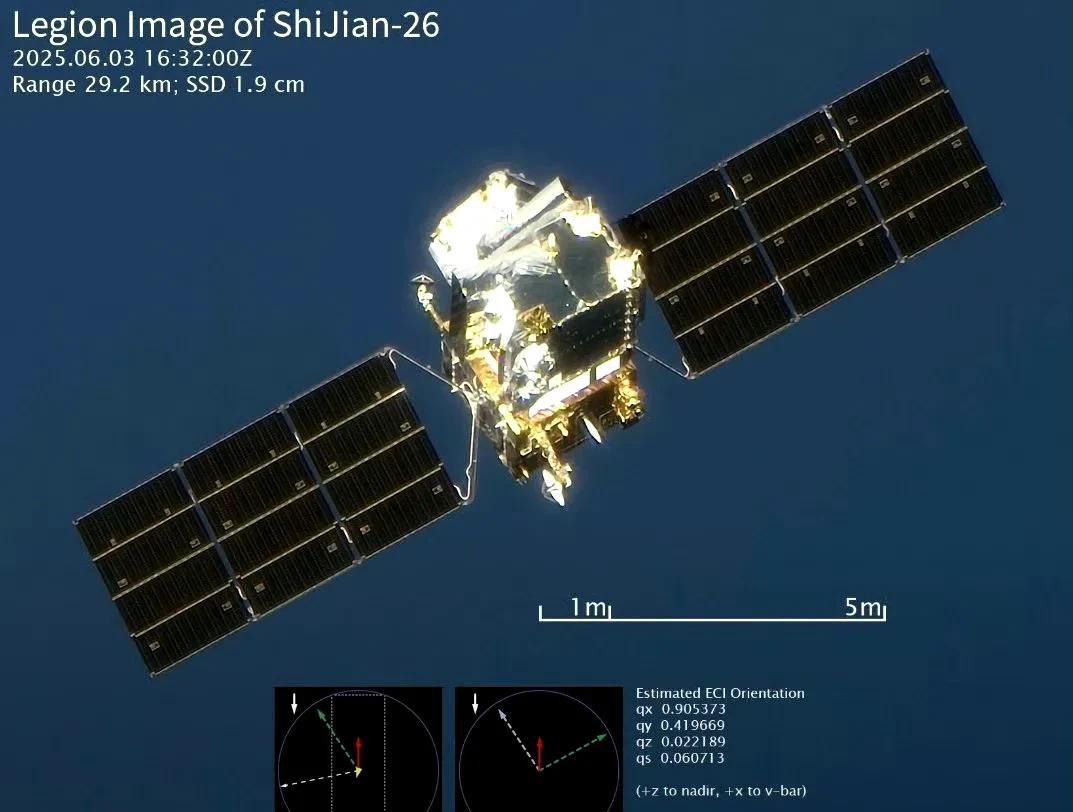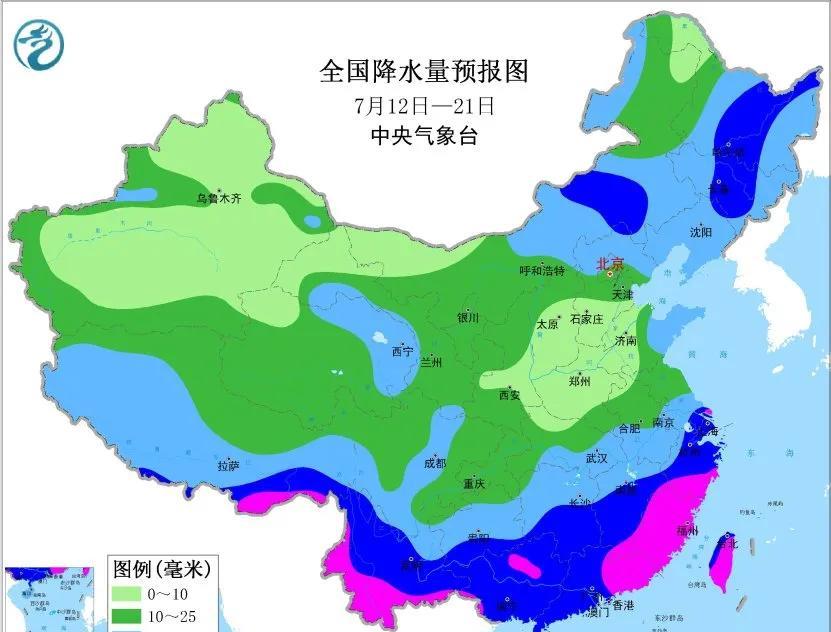1970 年,陈独秀 58 岁的女儿陈子美身绑 5 个空油桶,带着小儿子偷渡香港,9 个小时后,母子俩奇迹般抵达目的地,哪知,刚上岸就遇到警察,陈子美很是沮丧,不料,警察的举动让她大感意外。 珠江口的咸腥气裹着夜色漫过来时,陈子美把最后一根麻绳缠在手腕上。 五个锈迹斑斑的油桶在水里晃悠,小儿子的脸贴在她后背,温热的呼吸打湿了洗得发白的粗布衫。 她记得父亲陈独秀当年在上海办《新青年》时,钢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,可那些遥远的荣光,此刻远不如油桶接缝处渗出的海水实在。 三天前,小儿子在村口槐树下捡别人扔的红薯皮,被饿极了的野狗追着咬,她抄起扁担赶狗时,看着孩子胳膊上的牙印,突然就下了决心 —— 去香港,哪怕是死在水里。 她不会游泳,全凭听来的经验:涨潮时顺着水流漂,油桶能托住两个人。 出发前,她把藏在床板下的几块银元塞进儿子的裤兜,那是当年母亲高君曼留给他的念想,磨得边缘都圆了。 夜里的江水凉得刺骨,她能感觉到油桶在暗流里打转,有好几次,儿子的哭声差点被浪头吞没,她就用尽力气喊:“抓牢了,到了那边有白米饭!” 其实她也不知道香港有没有白米饭,只听逃出去的邻居说,那边的垃圾桶里都有没吃完的面包。 九个小时里,天从墨黑变成鱼肚白。她看见远处的灯火时,眼皮重得像挂了铅块。 油桶撞到礁石的那一刻,她以为是到了阴间,直到儿子扯着她的衣角喊 “有房子”,才发现自己趴在浅滩上,膝盖被贝壳划得全是血。 没等缓过劲,两个穿卡其制服的警察就举着电筒走过来,光柱晃得她睁不开眼。 她下意识把儿子护在身后,心想这下完了,要么被遣送回去,要么被关进牢里,早知道这样,还不如在水里淹死痛快。 警察的皮鞋踩在沙子上咯吱响,其中一个蹲下来,用生硬的普通话问:“从哪里来?” 她没敢说自己是陈独秀的女儿,只说 “广东乡下,活不下去了”。 另一个警察突然笑了,从背包里掏出个面包,递过来时还冒着热气:“先垫垫,看孩子饿的。” 陈子美愣了半天,接过面包的手一直在抖,面包渣掉在沙滩上,儿子狼吞虎咽地捡着吃。 她这才注意到,警察的制服袖口磨破了边,不像传说中那么凶神恶煞。 后来她才知道,那几年从珠江口漂来的偷渡者不少,警察见多了拖家带口的。 有个老警察说,看她头发都白了还带着孩子,实在狠不下心送回去。 他们没问她的名字,只给了她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个地址,说那边有同乡会。 她牵着儿子走在香港的街道上,看着汽车比村里的牛还多,突然就蹲在路边哭了。 不是因为委屈,是因为活着到了这里。 初来乍到的日子比水里漂着还难。她在纺织厂门口蹲了三天,才找到给人拆纱头的活,手指被纱线勒出一道道血痕。 儿子在附近的小作坊帮忙跑腿,常常被老板骂 “大陆仔”。有次她路过书店,看见橱窗里摆着印着父亲头像的书。 标题是 “新文化运动先驱”,她站了很久,终究没敢进去看。 同乡会的人知道她是陈独秀的女儿,想帮她联系媒体,被她拒绝了:“我现在就是个要饭的,别玷污了先人的名字。” 再后来,她在九龙的唐楼里租了个小隔间,窗户外就是别人家的晒衣绳。 儿子长大后开了家小小的杂货铺,逢年过节会给她买叉烧,她总说太甜,却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。 有回儿子问她,当年要是被警察送回去会怎么样,她看着窗外的雨,半天没说话。 其实她心里清楚,那天警察递过来的不光是面包,还有一条活路。 不是因为她是谁的女儿,只是因为她是个想让孩子活下去的母亲。 很多年后,有人找到她,想写她的故事,她指着墙上儿子一家的合影说: “没什么好写的,我这辈子,就做对了一件事,把娃带过了江。” 说这话时,阳光从窗棂照进来,落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,像当年漂在水里时,终于等来的那道曙光。 那些关于陈独秀的传奇,关于时代的风浪,最终都化作了唐楼里一碗热粥的温度,和儿子递过来的那杯热茶里,慢慢舒展的茶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