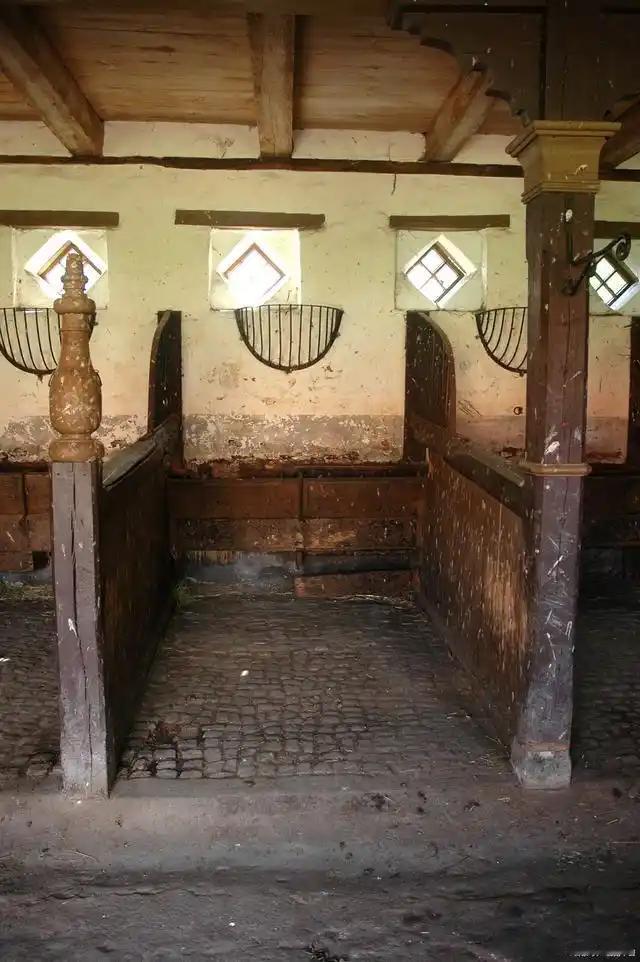古人是怎么上厕所的? 早期人类的厕所史始于大地本身的包容。 半坡氏族部落的房舍旁,那些不起眼的土坑正是华夏初代厕所的雏形。 西周时期,“隶人涅厕”成为定制:坑满即填,奴隶们挥动工具,将秽物连同隐私一同埋葬。 春秋时期,坑深加至三米以上,晋景公姬獳便是在这样的深坑旁失足跌落,成为史书里“陷而卒”的悲情主角——粪坑成了诸侯的终结者。 当农耕文明觉醒,粪便的价值被重新定义。春秋战国诞生了“溷轩”,巧妙融合厕所与猪圈功能,人蹲于高台排泄,秽物直落下方猪圈,与饲料残渣混合发酵为“沤肥”。 汉代陶楼模型清晰呈现了这一结构,架空干栏式厕位下接粪池,旁置虎子(溺器)与窬(粪桶),甚至有持帚妇人负责清洁。这种空间折叠术实现了排污与农耕的无缝衔接,堪称古代循环经济的先锋实验。 移动如厕的需求催生了古代版“随身厕所”。战国错金银鸟纹虎子现身贵族墓室,印证了夜壶的早期形态,是由青铜铸造的猛兽造型,张口承接主人的尿液。 唐代因避讳李虎之名,“虎子”变身“马子”,形制也悄然革新,容器扩大为桶状,兼顾固液收纳,“马桶”由此诞生。宋代杭州城内千家万户的木制马桶,由“倾脚工”穿街走巷回收,最终变作农田金肥。一只桶里,盛满了古人化解城市卫生危机的巧思。 贵族阶层的厕所则是另一番天地。 河南永城芒砀山汉墓中,梁孝王王后的石质坐便器令人惊叹,靠墙设长方形便坑,两侧石质坐垫配鞋型脚踏,靠背扶手俱全,更暗藏蓄水池与排水管,两千年前的冲水设计已然萌芽。 元代画家倪瓒的“香厕”更将洁癖升华为行为艺术:香木高楼下设敞口木格,覆盖轻盈鹅毛。秽物坠入瞬间,鹅毛如雪覆掩,仆人即时更换新格,以芬芳对抗污浊。 如厕后的清洁史,写满了人类的坚韧与尴尬。古罗马公厕里,绑在木棍上的海绵“Tersorium”是公共财产。 使用后浸入醋桶消毒便传递下一位,细菌在湿润孔隙中狂欢。古希腊人则偏爱陶片与石块,甚至将仇敌之名刻上陶片,在如厕时完成精神碾压。 中世纪的欧洲森林里流传着黑色幽默:“冬青树最干净,因无人敢用来擦屁股!”而在东方,佛教东传带来“厕筹”,二十厘米长的竹木薄片,三国时期已成主流。 元朝始用纸,但粗硬如砂,太子妃需以脸颊测试柔软度后方供皇后使用。1948年王耀武逃亡时因使用进口卫生纸暴露身份,一张纸竟改写历史。 古罗马公厕揭开了如厕的公共属性。半圆形石凳上凿孔密布,可容纳数十人并肩而坐,袍角褶皱成了唯一遮挡。 这里没有隐私羞耻,只有信息奔流,市民交换市井传闻,政客发表竞选演说,商贾洽谈生意。庞贝城厕所涂鸦泄露着古人心声:“提图斯皇帝的医生在此排便甚畅!”公厕成了古代版的社交媒体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