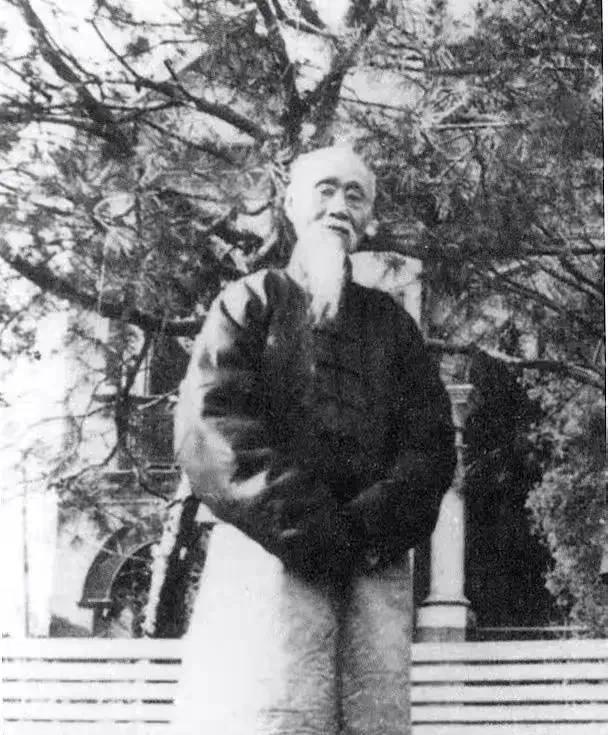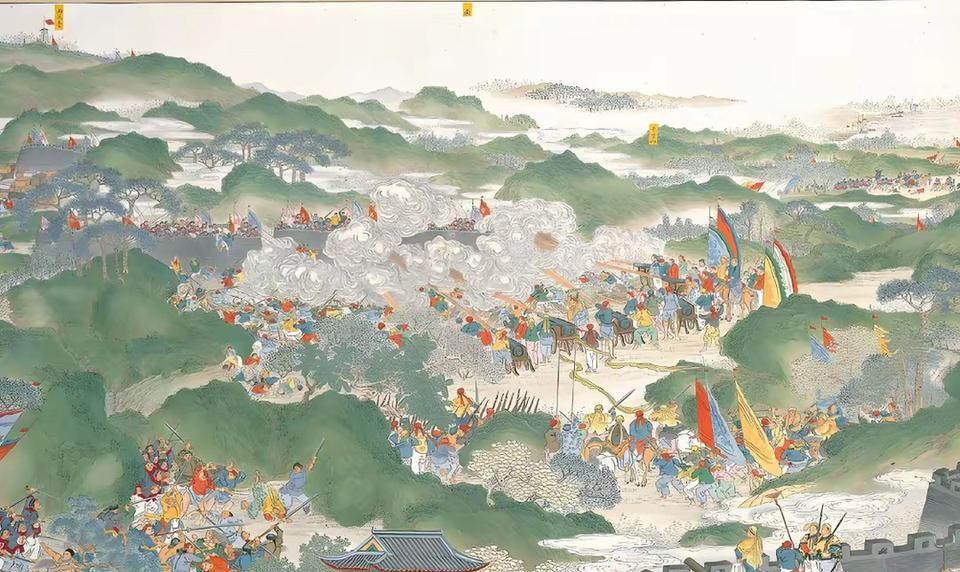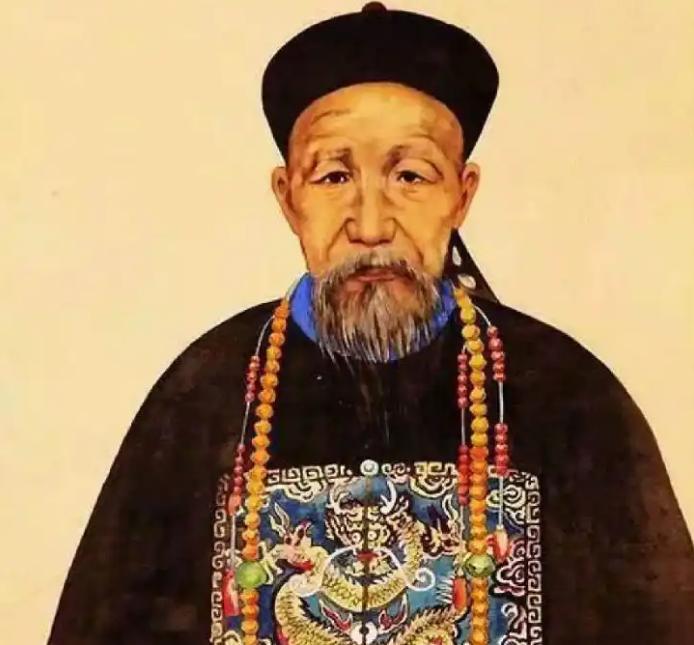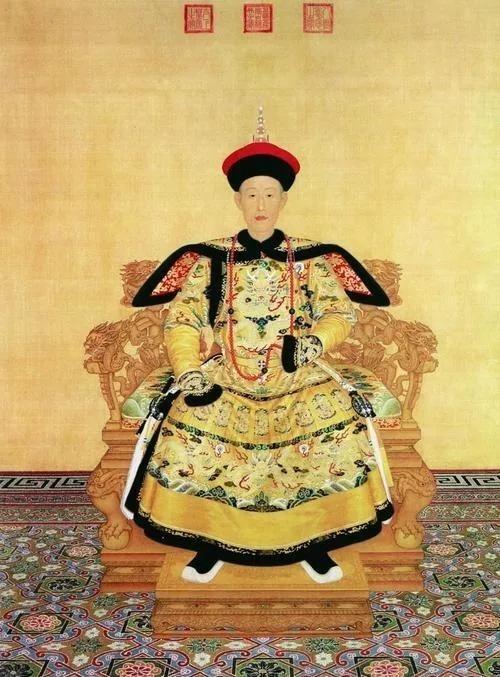1852年,母亲去世,二品侍郎曾国藩从湘乡县城步行五十里回家奔丧。那年夏天,湘乡烈日炎炎,曾国藩踩着滚烫的黄土路,官靴蒙灰,补服被汗水浸透。仆从荆七跟在后面直抹汗,心里嘀咕着老爷何苦如此,可曾国藩的步子越走越沉,眼神却越来越亮,仿佛每一步都在丈量着与母亲的距离。
十五年前离家时,母亲江氏送他到十里长亭,把攒了半辈子的碎银子全塞进他行囊,叮嘱“莫要贪凉”。此刻路边的野菊花黄灿灿开着,和当年母亲鬓边的绢花一个颜色。他蹲下身,抓起一把混着碎花瓣的泥土攥在手心,当年母亲就是踩着这样的土路,把晒好的腊肉送到县学给他加餐。如今物是人非,最后一面竟成永诀。
六月初接到讣告时,曾国藩正在安徽太和县境内,官船当即调头转道九江。逆水行舟的二十多天里,他总梦见母亲站在老宅门槛张望,醒来枕巾湿透一大片。村口的老槐树还是歪着脖子,树荫下几个光屁股孩童在捉蟋蟀。曾国藩怔怔望着,想起自己儿时在这树下背《论语》,母亲就坐在青石板上纳鞋底。蝉鸣突然尖锐起来,他恍惚看见母亲撩起围裙擦他额头的汗,可伸手只抓到燥热的风。
荆七说前头就是曾家新修的牌坊,他反而放慢脚步。当年离家时母亲乌发如云,如今灵堂里的棺木却已漆黑如夜。守门的老仆揉了半天眼睛才认出大少爷,一声“老太太等您啊”让他瞬间溃不成军。黄金堂的素幡被穿堂风掀起,露出后面“音容宛在”的匾额。曾国藩扑在棺木上时,榫头缝隙里飘出淡淡的檀香混着石灰味。他疯狂拍打棺盖要求开棺,族老们拗不过只得起钉。母亲面容比他想象的更安详,嘴角甚至带着若有似无的笑,仿佛只是睡着了在等他归来。
这个发现让他哭得更加撕心裂肺,母亲临终前指着柜子,家人搬出所有物件都不对,最后是父亲悟到她要摸儿子寄回的家书。那一大捆信被摸得起了毛边,最上面那封还沾着汤药渍,想必是病重时也要让人念给她听。灵堂烛火噼啪爆了个灯花,惊醒了昏睡中的曾国藩。他发现自己还攥着母亲入殓时穿的蓝布衫袖口,上面有他熟悉的补丁针脚。三弟国潢凑过来要扶他去休息,他甩开手又扑回棺前。这举动把满屋子人都吓住了,谁能想到平日最重礼法的二品大员,此刻竟像个撒泼的孩子。
其实他脑子里全是道光十九年冬天的场景,赴京上任前夜,母亲在油灯下给他缝棉袍,说“北方风硬,多絮层棉花”。现如今,那件棉袍早穿破了,可母亲指尖的温度似乎还留在肩头。夜深时下起小雨,瓦片上叮咚作响像谁在轻轻叩门。曾国藩突然起身往外走,族人们不敢拦,只远远跟着。他竟一路走到母亲生前住的厢房,从床底下拖出个落灰的樟木箱。箱里整整齐齐码着三十多双布鞋,从孩童的虎头鞋到官靴尺寸俱全。每双鞋底都纳着“平安”二字,最新那双的针眼还泛着白,分明是母亲病中强撑着做的。他抱着鞋子蜷缩在母亲床上,任凭晨光爬上窗棂。
出殡那日,曾国藩坚持要亲自抬棺。十六个杠夫拗不过,让他在前杠加了把手。黄土落进墓穴时,他突然想起十三岁那年贪玩落水,母亲背着他走了五里路求医。现在,终于轮到他扛着母亲了。可却不是为了就医看病,是永远的分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