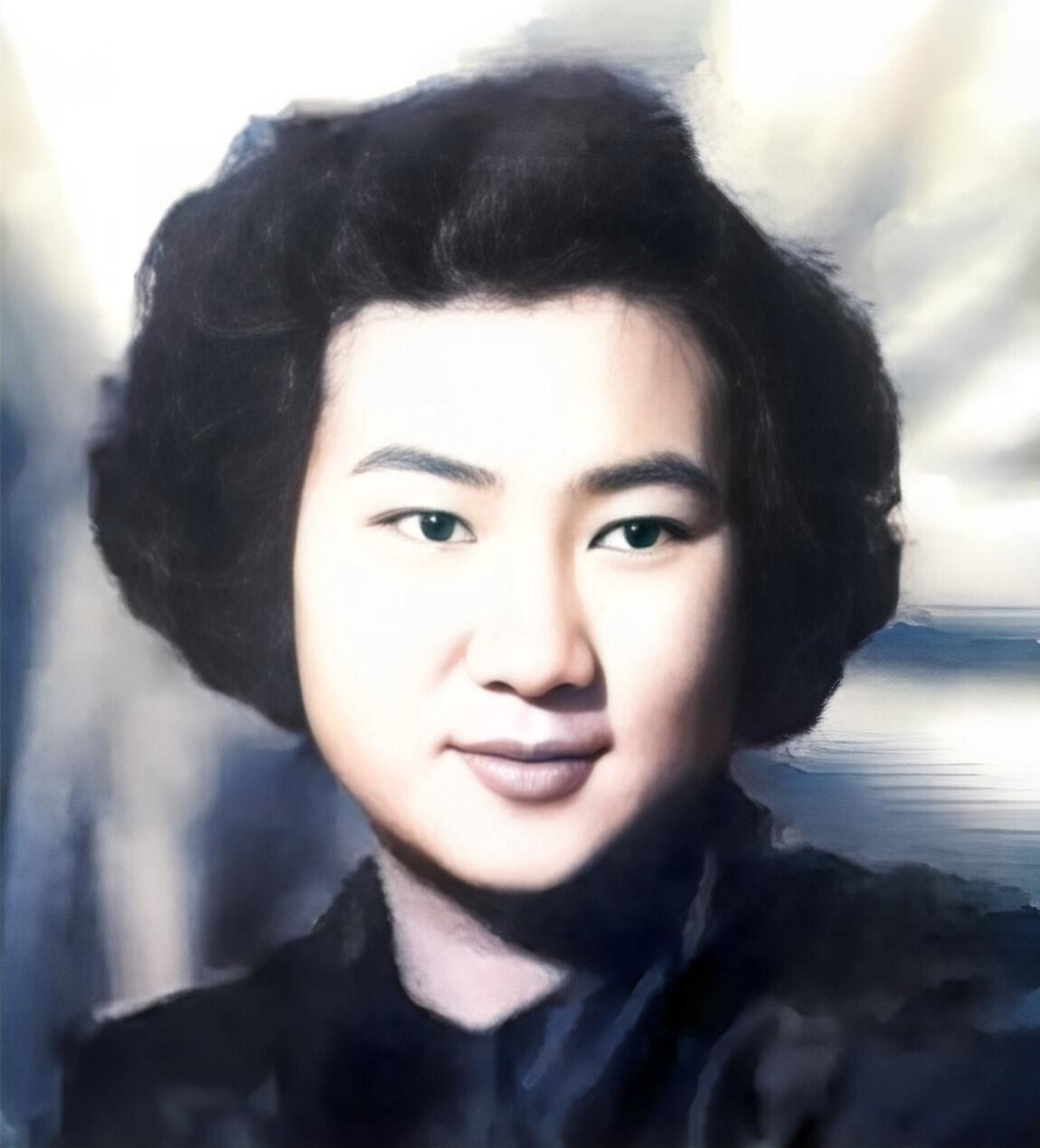1945年的昆明,一个中国小女孩被美国士兵开车撞死,却只赔偿了26美元,女孩父亲接过钱一言不发,不料,这惹恼了旁边一个美国人。 1945年深秋的昆明,李敦白坐在小巷入口的吉普车里,看着这位黄包车夫默默收下信封,深深鞠了一躬,然后转身走入昆明的烟雨中。 李敦白的心却沉到了谷底。 回想起他刚到昆明时的情景,一切仿佛还在昨天。那是1945年的9月,他和同伴乘坐运输机飞越险峻的驼峰航线抵达中国,不久便被派往昆明,担任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的中文专员。当时的昆明,是盟军从印度进入中国的关键门户,美国大兵的身影随处可见,而黑市交易更是繁荣兴盛——美国药品、Spam牌罐头肉、香烟、汽油,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流入当地人手中。 但在这繁华的表象下,是无数像李瑞山这样的普通中国人的辛酸生活。一个黄包车夫每天拉十二个小时的车,赚的钱最多只能让家人吃个半饱。 "黄包车夫李瑞山案"是李敦白接手的第一个案子。他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李瑞山时的景象:一个三十出头但看上去像四十多岁的男人,皮包骨头,胡子颓然下垂,光着脚丫,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。 "我们活着什么也没有了。"李瑞山平静地告诉他,声音中带着浓重的云南口音,"什么也没有,就是吃苦。我们就这么一个女儿,本来还指望她将来能过得好一点。" 那个悲剧发生在几个月前的一个清晨。李瑞山的独生女木仙在家门口踢毽子时,一辆美军卡车疾驶而过,将她撞死。肇事司机是一位空军军士,前一晚在城里的"巴黎街"夜总会狂欢后,又灌了两杯威士忌"醒醒宿醉",开车回营地途中,他看到小木仙在踢毽子,竟起了恶作剧的念头。 "我就告诉自己,我要看看自己能开得靠那个邋遢小女孩多近,"司机在口供中说,"但是天杀的,我要是没有撞上她就好了。然后我就想着尽快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。" 李敦白走进李瑞山的小屋时,看到木仙的母亲木愣愣地坐在那里,两眼呆滞地盯着墙壁。自从亲眼目睹女儿被撞死后,她再也没说过一句话。 回到赔偿部,李敦白写了详细报告,建议给予最高额赔偿。但几周后,助理理赔官只批准了区区二十六美元的赔偿金。而在同一时期,另一个美军卡车撞死商人小马的案件,赔偿金竟高达一百五十美元。 当天下午五点,李敦白正准备收拾东西下班,办公室门口却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——李瑞山竟然跋涉数里,穿过层层守卫,站在了他的办公桌前。这位黄包车夫手里拿着一个用破纸糊的信封,恭敬地递给了他。打开一看,里面竟然装着六美元。 "这是做什么?"李敦白困惑地问道。 "谢谢你的帮助。"李瑞山平静地回答。 一瞬间,李敦白明白了什么,他小心翼翼地追问:"你是不是也包钱给甲长呢?" "是的。"李瑞山回答。 "也给了保长?" "是的。" 这简短的对话如同一道闪电,照亮了李敦白心中的黑暗。在李瑞山的世界里,他不过是众多需要打点的官员中的一员。即使在女儿惨死、妻子精神崩溃的悲剧后,这位中国父亲依然认为必须按照"规矩"行事——将那微薄的赔偿金分给每一个经手的人,包括撞死他女儿的外国军人的同事。 当李敦白说出"规定"两字时,李瑞山脸上竟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。在他的世界里,"规定"从来都不是保护弱者的盾牌,而是强者用来维持秩序的工具。这个笑容背后,是几千年来形成的对权力的理解和屈服。 李敦白坚决地把信封还给了李瑞山:"我不能收。这样做是违反规定的,而且无论如何我都不应该拿你的钱,这份赔偿金实在太少了。"李瑞山只是鞠躬致谢,然后转身离开了办公室,从此李敦白再也没见过他。 后来李敦白了解到了整个索赔流程的复杂和腐败。昆明的居民大部分不识字,他们要索赔,必须先找掌管十二户的甲长,再由甲长将申诉转呈给管理十二个甲长的保长。之后保甲长会共同用毛笔将索赔案写在宣纸上,上呈县政府,最后才由县政府交给美军。在这层层转递中,每个经手的中国官员都从这个不幸的索赔者身上榨取一份"油水"。谁要想逃避这种盘剥,就会遭到百般刁难。 李瑞山一家的悲剧和随后发生的事情,让李敦白对美军和当时的社会现实产生了深刻的失望。二十六美元对一个女孩的生命,六美元作为"感谢"——这两个数字在他心中不断回响,像是两记重锤,敲碎了他对自己身份和使命的认识。 这种失望最终推动李敦白与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。地下党的负责人给他取了个中文名字:李敦白。这个名字选自大诗人李白的名字,中间加了个"敦"字,代表正直,与他的英文名"Rittenberg"谐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