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上海人回到“邯郸学步” 在上海住满十二年,腊月二十九的虹桥站,人推着人,像黄浦江涨潮,把你一直往北推。高铁一过长江,窗外的光景就变了——也说不上哪里不同,只觉得天色暗了一层,像是谁用旧毛玻璃把窗户挡了一挡。 邯郸站出口的地方,堂哥一把拍在你肩膀上:“嘿,上海佬回来了!”那声“上海佬”,裹着一股子烟味和鞭炮味儿,热烘烘地喷在你脸上。你扯着嘴角笑了笑。脚下的水泥路是新铺的,又平又宽,可你走着走着,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奇怪,在上海挤了这么多年地铁,闭着眼睛都能从人民广场换乘到陆家嘴,怎么回到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,反而不会走路了? 老街还在,只是窄了许多。两边的房子像是被什么压矮了一截,记忆里高高的屋檐,现在一抬手就能够着。青石板早就没了,铺上了一色的灰砖。你想学着小时候那样,跳着格子走,腿脚却沉得抬不起来。几个孩子“嗖”地从你身边跑过去,鞋子拍在砖上,“啪啪”地响,又脆又亮。你晃了一下,差点崴了脚。背后有人笑:“……到底是上海回来的,走路都不一样。”你转过头,是个不认识的婶子,脸上笑得皱成一团。你脸上有点热,那句“不一样”,怎么听都像是在说“格格不入”。 大年三十,一大家子围着炉子守岁。热气混着瓜子花生的香味,熏得人昏昏的。你那些“KPI”、“用户体验”的词到了嘴边,又咽了回去。舌头像是打了结,说出来的家乡话,自己听着都别扭,像收音机里调不准台的杂音。父亲聊起今年的麦子价钱,西头老王家娶媳妇要了多少彩礼,你听着,想接话,却总是慢了半拍。盘腿坐在炕上,总觉得腰背挺得太直,像是还坐在公司那把转椅上,怎么坐都不舒坦。起身的时候,你下意识地侧了侧身,让长辈先走。父亲看了你一眼,没说话,眼睛里的光闪了闪,又暗下去。 初一的晚上,和老同学们喝酒。当年一起逃课翻墙的兄弟,现在一个个都有了肚腩,说的都是房子、车子、单位里那点事儿。酒喝到一半,划起本地的酒拳。那些弯弯绕绕的手势、又急又快的口诀、土得掉渣的词儿,你早就忘光了。伸出去的手僵在半空,笨得像是第一次拿筷子。满桌子的人哄堂大笑,你只好一杯接一杯地喝。酒辣得烧喉咙,一直烧到胃里,像是要把这些年在外头沾染的东西,都烧个干净。 散场的时候,街上已经没人了。爆竹的红纸屑铺了一地,空气里还有硫磺的味道,闻着有点呛鼻。路灯把你的影子拉得老长,又缩得很短。影子晃来晃去,一会儿像那个每天挤二号线去静安寺上班的你,一会儿又像许多年前,在巷子里滚着铁环疯跑的你。两个影子扭在一起,谁也压不过谁。 你忽然就懂了。那种不会走路的感觉,是从哪儿来的。 在上海,你学的是另一套走法。地铁门一开,身子就自动侧过去,顺着人流挤出去,这是“赶路步”;在安福路买杯咖啡,要慢悠悠地晃,眼睛看着橱窗,这是“闲逛步”;在会议室里,步子要稳,要沉,要跟着说话的节奏,这是“场面步”。十二年,你把这些步子走得滚瓜烂熟,以为那就是你了。 可家乡要的步子,不是这样的。它要的是扛着锄头下地,一脚深一脚浅踩在泥里的“庄稼步”;是红白喜事里,跟着唢呐声,该哭就哭、该笑就笑的“人情步”;是冬天靠在南墙根,晒着太阳,一步三晃的“懒人步”。 这些步子,你生来就会的,就像天生会吃饭喝水一样。可现在,全丢了。上海的步子,在这片土地上踩不出声音;家乡的步子,又在这些年里生了锈。你像是站在两座桥的中间,哪一头都够不着。 古书里那个邯郸学步的少年,去别人那儿学走路,最后连自己怎么走都忘了,只好爬着回家。你呢?你这一趟,算不算是“上海学步”?学了十二年,回来却忘了本来的样子。 风刮过来,你裹紧大衣。蹲下身,摸了摸地上的砖。凉的,硬的。昨天陪母亲去庙里,佛殿前头有块石头,被来来往往的人踩了几百年,磨得又光又亮,像面镜子。求神的,拜佛的,许愿的,还愿的……成千上万双脚从上面走过,什么样的步子,最后都留在这块石头上了。 你站起来,不再去想上海怎么走,邯郸怎么走。只管朝着有灯光的地方,一脚轻,一脚重地走回去。 远处不知哪家又放了一挂鞭炮,“噼里啪啦”地炸开,惊起树上一只麻雀。那麻雀扑棱着翅膀,慌慌张张地飞进黑夜里,也不知道要飞到哪儿去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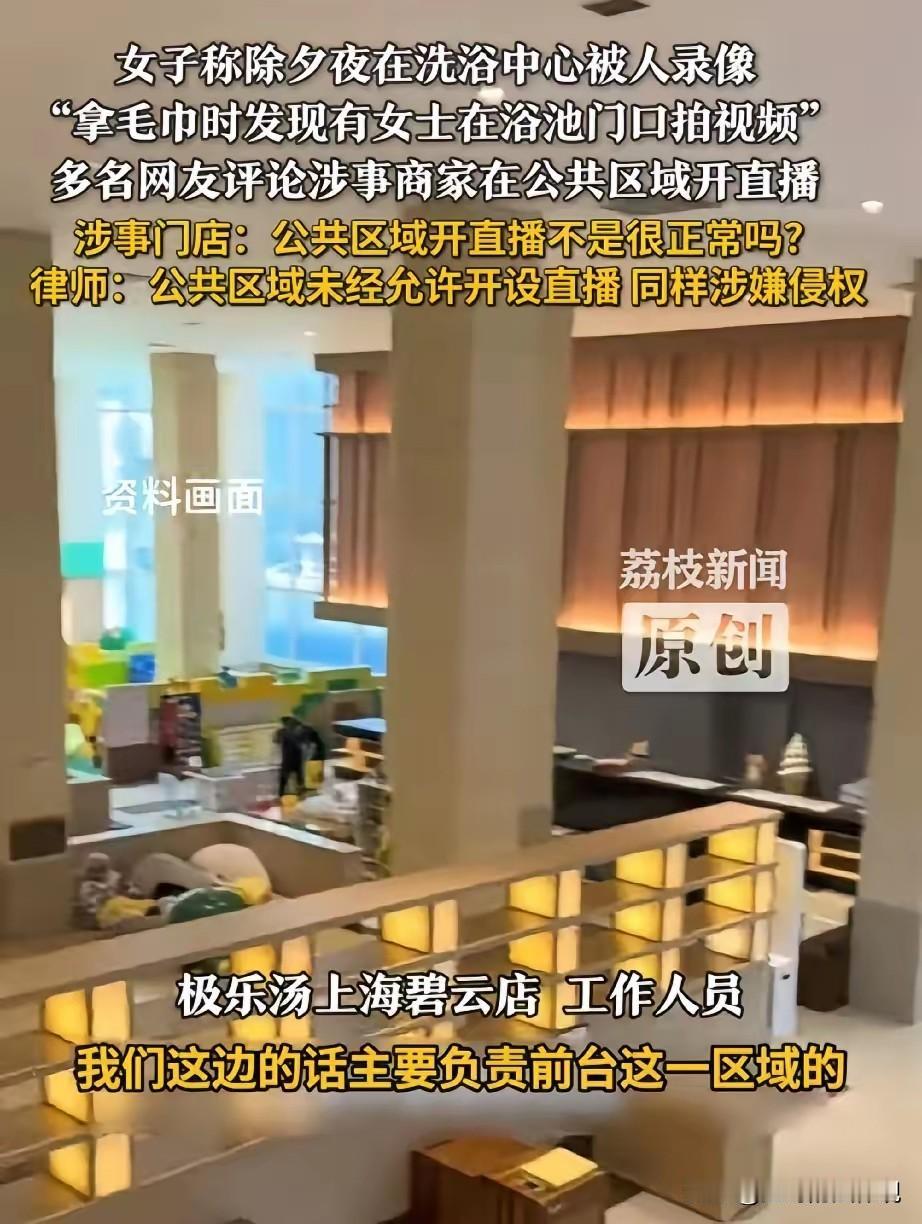





银光之翼
我也是外地来上海的,差不多20年了。我最奇怪的就是现在很多人一边数落上海这不好那不好,但就是不肯回老家。热爱家乡当然是好事,但没必要数落你现在生活的城市,毕竟那里给了你工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