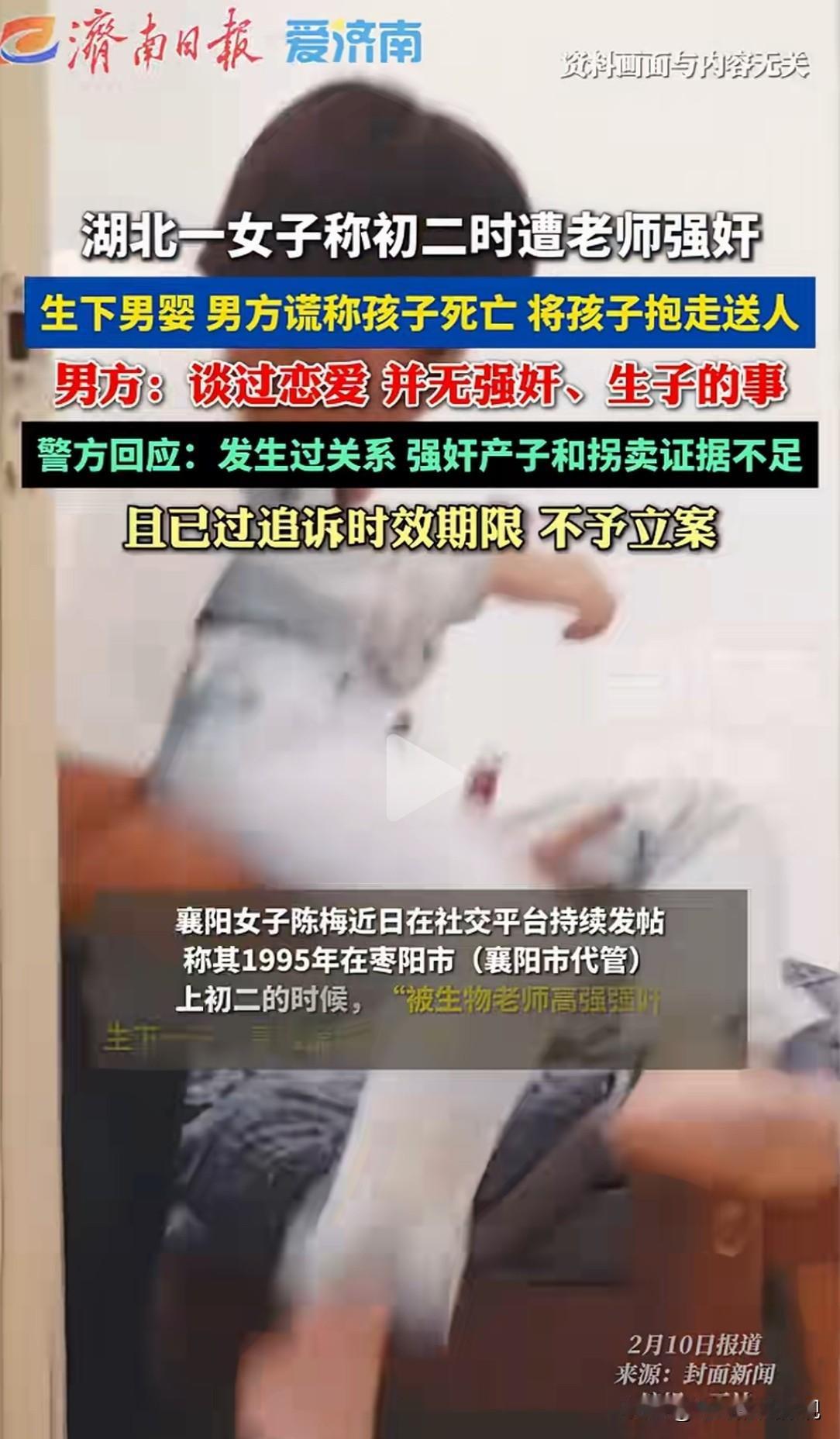河南郑州,一60岁男子在小区花园里带孙子,结果碰到同小区的7岁女童也在带着弟弟玩耍,因为之前打过照面,男子认识这名女童,所以就将女童引导至石凳旁,随后男子对女童实施了猥亵,事发后,女童家人觉得判轻了申请检方抗诉,而男子则表示愿意给3万元求原谅。 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的空气里,漂浮着两组截然不同的算术题。 2026年2月2日,这一天的庭审现场,被告席上的殷某某抛出了他的筹码:3万元。这个数字被小心翼翼地推向原告席,试图买断一张“谅解书”。对于一个已经60岁的老人来说,这张纸意味着二审判决可能从轻,甚至就在2年刑期内打转。 而在法庭的另一侧,受害者彤彤的母亲吴女士和律师,死死盯着另一个数字:5年。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讨价还价。仅仅数月之前,一审判决结果揭晓,被告仅获有期徒刑两年。此结果,或引发众人对司法裁量的深思。对于一个有过强奸罪、抢劫罪前科,且对邻居7岁幼女下手的累犯来说,这个判决轻得让吴女士感到脊背发凉。她没要那3万元,而是选择了那条更艰难的路——申请抗诉。 好在,检察院站在了母亲这边。 若要厘清此事逻辑,不妨将时间的指针拨回2025年2月4日的那个午后。彼时种种,或许能为当下的谜团,勾勒出清晰的脉络。 那天是大年初七,过年的气氛还没散。7岁的彤彤领着年仅2岁的弟弟在小区花园嬉闹玩耍,不经意间,恰好与同样带着孙子外出的邻居殷某某相遇。因为两家孩子一般大,大人平时见面也会点个头,这层“熟人”的滤镜,成了最致命的掩护。 殷某某领着彤彤,踱步至花园的一处石凳旁,一边走着,一边柔声说道:“乖孩子,让爷爷瞧瞧,究竟生得多么标致。”在那个被灌木和建筑遮挡的角落,那只左手伸进了女孩的上衣。从肚子一路向下,直到触碰隐私部位。剧痛让彤彤尖叫出声,这声叫喊打断了暴行,也把这个看似慈祥的邻居拽回了现实。 尽管医院检查报告表明“外阴及处女膜无显著破损”,然而从法律层面而言,此情况并不妨碍对“猥亵既遂”的判定。真正的争议焦点在于,此情形究竟能否界定为“于公共场所当众”?这一判定不仅关乎事实认定,更涉及法律适用的精准性。 这是一个极其微妙的法理博弈。 按照刑法第237条的标尺,猥亵儿童罪的基础刑期是5年以下。若想突破此上限,获判五年以上刑罚,需具备“聚众”或“于公共场所当众”这类恶劣情节。如此情形下,司法裁量会考量情节的严重程度。 一审法院判2年的逻辑大概率在于此:虽然小区花园是绝对的公共场所,但殷某某特意挑选了死角,避开了人群视线。在那个瞬间,除了当事人,没有“第三只眼”看到。这种隐蔽性,反而成了他逃避重刑的法律救命稻草。 但检方这次没有沉默。 2025年11月14日,上街区检察院作出明确回复。其认为一审量刑明显过轻,有悖司法公正,遂决定启动抗诉程序,以彰显法律之严谨与公平。这两个字的分量极重。在刑事诉讼里,若被告人提出上诉,依据原则,遵循“上诉不加刑”之规定。此旨在保障被告人上诉权利,使其不必担忧因上诉而遭受更重刑罚。但如果是检方抗诉,这个保护机制瞬间失效,二审法院完全有权改判更重的刑罚。 2月2日的二审庭审中,检方的建议量刑提到了4年以上,受害人律师更是直接咬定5年以上。这不仅是因为那几分钟的罪行,更因为殷某某档案里那个刺眼的“强奸罪、抢劫罪”前科。一个曾经被判过4年刑的人,再次向幼童伸出手,司法系统显然认为2年的代价不足以震慑这种恶念。 场外的博弈比庭上更见人心。 殷某某家属所提的3万元赔偿诉求,吴女士认为“这绝非单纯的金钱事宜”,其中蕴含的意味远不止金钱本身。在一审后的漫长时间里,殷某某一方并未表现出真正的歉意。相反,吴女士称对方家属在小区里对他们进行“反向施压”:对着受害家庭拍照,甚至对着小孩子做怪动作吓唬。 这种“二次伤害”的后果是具象的。那个曾经活泼的彤彤不见了。现在的她,换衣服要反锁房门,不仅不爱出门,甚至对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产生了应激性的防备。 即便殷某某被捕伏法,那阴暗角落也未就此消弭。它如一颗毒种,悄然被移植进一位年仅七岁女孩的心灵深处,在那里生根潜藏。 二审庭审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,法槌尚未落下最终的定音。但这起案件已经撕开了一个口子,让我们看到:当法律的“技术细节”与大众的“朴素正义”发生摩擦时,司法机关如何通过抗诉机制进行自我校准。 毕竟,对于吴女士和彤彤来说,那3万元买不回安全感,只有那一纸加重的判决书,或许能稍微堵上那个心里的黑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