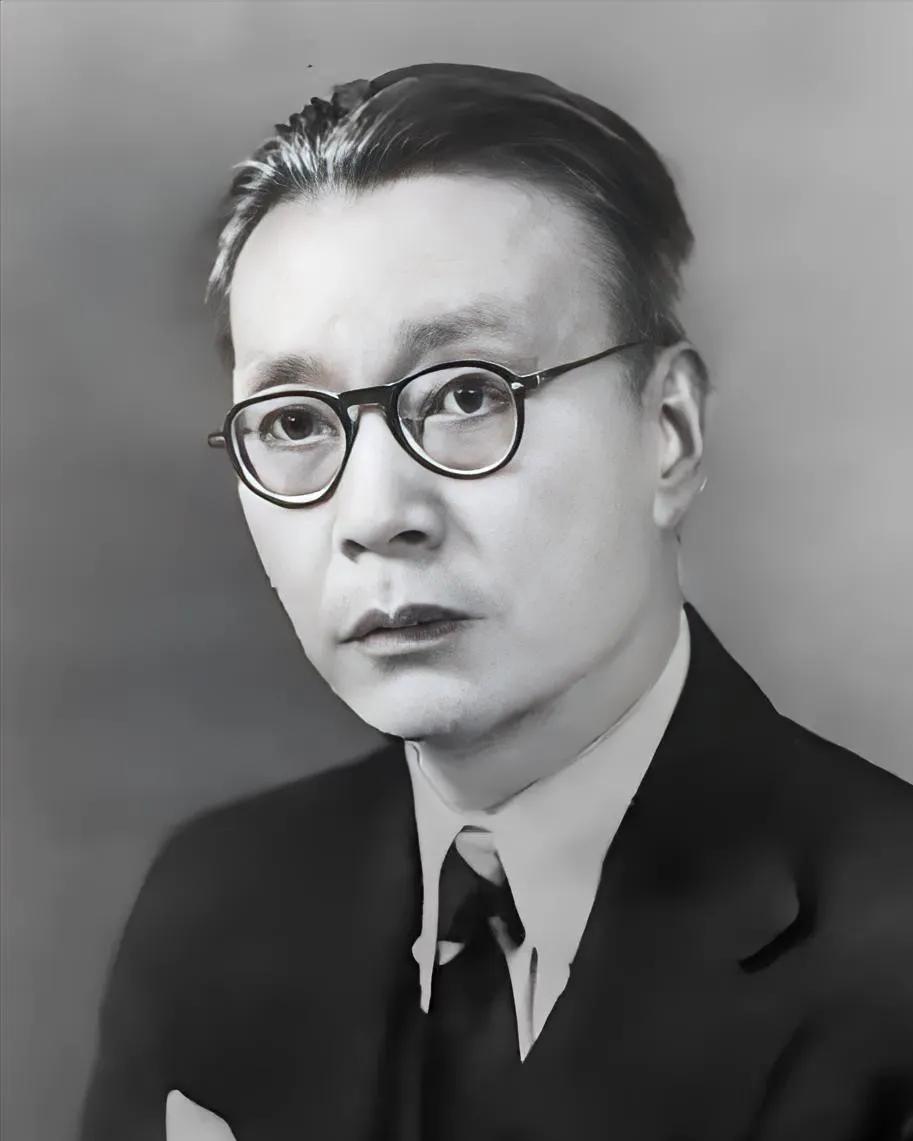1965年,62岁陆小曼去世。翁瑞午的长女翁香光闻讯赶来,见四下无人,迅速解开陆小曼的衣扣,眼前的场景令她惊愕不已,忍不住感慨:凉薄之人终究没有好下场 陆小曼出身上海显赫人家,从小按名门闺秀来培养,外语、绘画、京剧样样不缺,少年时期已在北京社交场如鱼得水。 婚姻却一路踩在别人的雷区上,从听命而嫁的军官夫人到冲破伦理的“新式恋爱”,一路走来始终站在舆论的刀尖。 与王赓的结合带来的是无聊日子,与徐志摩的结合则是灯红酒绿与争吵交织,背后还有一个始终不肯认账的徐家长辈。 表面上看,陆小曼一生被三个男人托着向前走。年轻时有王赓的军功、徐志摩的才情,中年以后又有翁瑞午的财力。婚后在上海,陆小曼花费极大,徐志摩四处兼课写稿支撑家用,直到那次飞往北京的航程永远停在济南上空。 徐家人后来始终认定,这趟没有保险的廉价航班,与陆小曼的消费压力脱不开关系。等到翁瑞午出现,陆小曼已离不开鸦片和药物,这位银行家卖了房子卖古董,几十年里把所有收入几乎都投进陆小曼的生活和治疗,却一直没有走进婚姻登记簿的一栏。 在外界的长久记忆中,陆小曼仿佛一直停留在那张穿旗袍、画浓妆的老照片里。现实里的后半生却苦得很。鸦片留下的后遗症日益加重,肺气肿和哮喘让每一次呼吸都像打一仗。 进入上海中国画院以后,陆小曼终于有了名正言顺的职业身份,画山水画花鸟,参加展览,作品有人买,画室里看上去一派雅致,账本上却是药费和住院单一张盖着一张。 病情最重的时候,陆小曼甚至在病床上画完最后一幅自画像,似乎在给自己这一生做个收尾。 真正把这场人生悲剧推到极致的,是临终和身后这两道关口。病危时,陆小曼对友人明说自己熬不过六十二岁这个坎,反复提到经常梦见徐志摩,心里挂念的也只有和徐志摩合葬这一件事。 对几十年来衣食住行几乎全靠的翁瑞午,却几乎不见一句公开的道谢。翁瑞午临死前,还要牵着女儿的手拜托继续照顾陆小曼,等到女儿在医院给陆小曼换衣服时,看到的却是贫穷和疾病共同刻下的痕迹,难免心中五味杂陈。 遗愿传到徐家,得到的回音很直接。徐申如当年拒绝出席婚礼,对陆小曼从未认同,徐积锴延续了这种态度。在徐家人看来,徐志摩去世前夫妻矛盾重重,陆小曼日后又与翁瑞午同居多年,无论从家族伦理还是现实情感,都不再适合躺进徐家的墓地。 于是,陆小曼惦念多年的合葬成了空话,火化后无人张罗安葬,骨灰在殡仪馆几次搬迁中失了踪影。等到堂侄在苏州东山华侨公墓为陆小曼立起衣冠冢时,只能把生前用过的笔墨碗筷埋进土里,用六个字和一串小字简单交代这一生。 从远处看,这是一场“因果循环”的人生。年轻时候享受着出身和才华带来的万千宠爱,却在婚姻里屡屡踩人底线,对身边最亲近的人时常忽略别人所付出的代价。 几十年下来,徐家把大门关得紧紧的,翁家心中有一块始终化不开的硬石,等到真正需要有人为生命的最后一程出力时,能站在床边的人少之又少。 可如果走近一点,又不免生出几分怜惜。那个在画案前挥毫的女人,的确有真才实学,在中国画院留下的作品不是空穴来风。那个在病床上回想一生的女人,眼里仍然紧抓着一份早早破碎的爱情,把其余人和事都摆在后面。 选择与性格交错,温柔与凉薄同身,最终共同塑造了陆小曼这段既耀眼又凄清的轨迹。清明时节,风吹过东山那块小小墓碑,留下的只有几个字和后人不一而足的评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