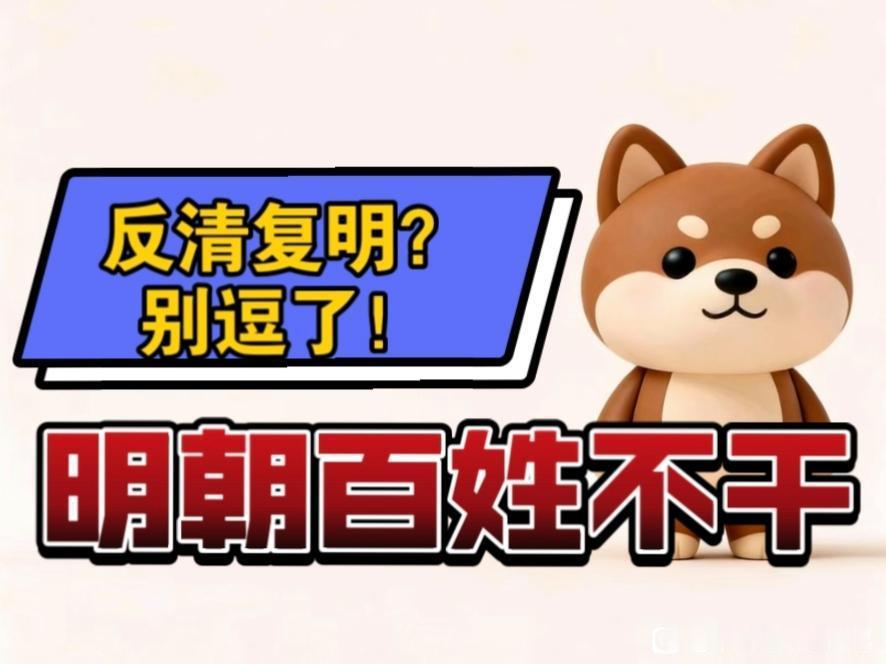汉字不能被毁灭!美国人在发明电脑的时候,压根就没想过要使用把汉字输入法。 要把时钟拨回到1984年9月的纽约联合国总部。那一天的现场气氛诡异而紧绷,一台连接着庞大主机终端的黑色屏幕前,一位来自中国的技术人员正在敲击键盘。这本该是一个极其枯燥的演示环节,但站在一旁的红头发联合国副秘书长,眼神里却充满了不可思议,甚至带着一丝警惕。 随着键盘的哒哒声,屏幕上并没有出现预期的乱码或拼音,而是一行行白色的方块汉字在黑色背景上疯狂跳动,速度快得惊人。演示结束后,那位副秘书长做出了一个极其“外行”却又意味深长的动作:她走上前,一把将键盘底朝天翻了过来。她在找机关,她怀疑这块键盘底下藏着特殊的电路或者作弊器。 除了那26个通用的字母键,她什么也没发现。当天,美国媒体发出的报道标题只有寥寥几个字:“举世称难,今迎刃而解”。 但在那之前的几十年里,西方计算机界的共识冰冷而傲慢: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。 这不是什么危言耸听。在七八十年代,计算机的内存是以KB为单位计算的。对于只有26个字母的英语世界,这点空间绰绰有余。但对于拥有数万个字符的汉字体系,这简直就是物理层面上的绝杀。当时的主流论断是,中国想要进入信息时代,唯一的出路就是废除汉字,彻底走拼音化、拉丁化的道路。 这种绝望感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达到了顶峰。全球七千多名记者都在用电脑敲击稿件,唯独中国记者还趴在桌子上用钢笔手写。那个画面,像极了两个时代的对撞。 被逼到墙角的,不只是汉字,还有像王永民这样的技术狂人。 早在1978年,还在河南南阳科委当办事员的王永民,就被一台日本引进的“汉字照相排版植字机”给刺激到了。那台机器笨重得像个怪物,为了输入汉字,日本人设计了24张幻灯片,每张片子上密密麻麻排了273个字。要打一个字,得先翻片子,再找坐标,效率低得令人发指。 王永民在鉴定会上直接质疑这种反人类的设计,结果被川光厂的总工当场嘲讽:“你懂什么?给我当徒弟再学三年吧。”王永民没说话,回头就立了军令状,要了3000块钱研发经费,发誓要让汉字直接住进标准键盘。 这是一场暴力拆解与哲学回归的博弈。为了把汉字塞进那26个按键,王永民把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里的一万两千个汉字,硬生生拆成了12万张卡片。 在他那间只有30平米的办公室里,卡片铺满了地面,连角落里都堆满了装卡片的麻袋。他没有去死磕西方的逻辑,而是掉头向后,回到了老祖宗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。 “独体为文,合体为字”。他发现汉字看似浩如烟海,其实骨架是有限的。通过归纳出字根,他把原本需要的188个键位,一步步压缩到了36个,最后定格在25个。这是一场算法的暴力美学——把成千上万的图形字符,通过逻辑重组,折叠进了这一方小小的键盘里。 这不仅仅是王永民一个人的战斗。就在他解决“怎么入”的问题时,另一位技术天才王选正在解决“怎么存”的问题。 面对内存不足的死局,王选抛弃了西方通用的点阵像素存储法,改用“矢量数学公式”来描述汉字的笔画骨架。这直接将存储空间压缩了数千倍,让汉字摆脱了内存的勒索。而倪光南则搞出了“联想汉卡”,让电脑学会了“猜”人话,你敲一个字,它能自动联想出一串词。 这套组合拳,硬生生把汉字从被淘汰的悬崖边拉了回来。 然而,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,当1984年王永民在联合国享受高光时刻时,他在北京的真实生活却正处于至暗时刻。 回到国内的他,住在一间潮湿的地下室里,每天在这个城市的各个部委之间奔波推销,骑着一辆破自行车,早饭常常是窝头咸菜。因为肝病复发,他的口袋里甚至常年揣着一份6000字的遗书。 最讽刺的是,真正让这位中国发明家走出地下室的,不是体制内的经费,而是一笔来自大洋彼岸的交易。1986年底,美国DEC公司支付了20万美元购买了五笔字型的专利。这笔来自“曾经质疑者”的巨款,才让王永民交上了拖欠已久的7块钱房租,也让这项技术真正拥有了造血能力。 随后,IBM、微软、苹果等全球IT巨头纷纷跟进购买专利。那些曾经断言“汉字无法数字化”的西方公司,最终不得不掏钱购买让汉字进入数字世界的门票。 这场技术突围的余波,最终在行政层面敲下了一记重锤。 1985年12月,国家将“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”正式更名为“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”。仅仅是去掉了“改革”二字,却意味着那场持续了半个世纪、试图将汉字拉丁化的历史大讨论,在数字化浪潮面前彻底终结。 既然汉字能顺畅地跑在光缆和芯片上,那还有什么理由废除它? 如今回看,这不仅仅是几个输入法或几行代码的故事。这是一群技术人在悬崖边上的背水一战。他们证明了古老的象形文字不需要向只有26个字母的机器逻辑下跪。 参考信息:人民网. (2013 年 9 月 28 日). 王码五笔字型发明人王永民回首汉字输入这 30 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