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十年代时,村里有一个男孩,人很聪明,高中毕业后,被大队安排在卫生所,炮制个药,抓个药,给卫生所干个杂活,他善于心计,抓药时留意医生们开的药方,买了药书,在老医生的指导下不断学习着,还拜了师,几年后就能治疗常规发病,后经县卫生局统一考试,合格成为一名赤脚医生。 村里人喊他狗剩喊了十几年,直到红皮资格证递到手里,才有人试着叫“李医生”。但他那只帆布药箱还是老样子,边角磨得发白,侧面蓝墨水写的“卫生”二字被岁月晕成了一团,里面装着酒精棉、镊子,还有本翻得起毛边的《农村常见病防治手册》。 那年秋天,村里二柱家的娃掉进开水锅,烫得小腿起了燎泡。二柱媳妇抱着娃哭得上气不接下气,狗剩背着药箱往他家跑时,太阳刚落山,天边剩点橘红色的光,田埂上的蚂蚱蹦得老高。到了屋里,娃哭得嗓子都哑了,腿上的泡亮晶晶的,像揣了一兜子水。二柱蹲在门槛上抽烟,烟锅子“吧嗒吧嗒”响,火星子掉在地上,烫出小黑洞。 狗剩把药箱往桌上一放,帆布冻得硬邦邦,发出“啪嗒”一声。他翻出烫伤膏,又从底层摸出个小瓷瓶,里面是他用獾油和冰片熬的药膏——老医生说这方子治烫伤最管用,他去年冬天熬了小半瓶,一直没舍得用。给娃涂药时,娃哭得更凶,狗剩空着的那只手在兜里摸了摸,掏出颗水果糖,是他去公社开会时,供销社老张塞的,纸都皱了。“含着,甜的。”他把糖塞进娃嘴里,娃含着糖,哭声小了点,眼睛还泪汪汪地盯着他。 涂完药包扎时,二柱媳妇端来碗热汤,“狗剩,喝口暖暖。”他摆摆手,正给绷带打结的手顿了顿——刚才跑太快,药箱撞在门框上,里面的紫药水洒了点,把帆布染了块紫斑,看着像新添的记号。“明早我再来换次药,别让娃抓绷带。”他背起药箱往外走,二柱跟在后面塞鸡蛋,他没接,“家里留着给娃补补。” 走在田埂上,月亮上来了,把影子拉得老长。药箱里的玻璃瓶碰撞着响,他想起刚去卫生所时,老医生教他认草药,“这是蒲公英,叶子锯齿状,治上火”,说着就掐片叶子让他嚼,苦得他龇牙咧嘴,老医生却笑,“良药苦口嘛”。现在他自己也成了“医生”,才明白那苦里头,藏着点别的滋味。 后来那娃腿上没留疤,长大了见了他还喊“狗剩叔”,不喊“李医生”。村里人说狗剩傻,放着轻快活儿不干,偏背着药箱跑东跑西。他听了也不恼,蹲在墙根晒太阳时,拿手摩挲着药箱上的紫斑,像摸着块宝贝。现在村里卫生站盖得亮堂,年轻医生穿着白大褂,可老人们凑一起还说:“当年狗剩那药箱,比啥都管用。”你们那儿,有没有哪个旧物件,一提起来就让人心里发热?
泪目!河南郑州,一家人在妇幼门口等着,娃刚落地,左眼皮上贴着一团肉,把眼睛压住了
【3评论】【2点赞】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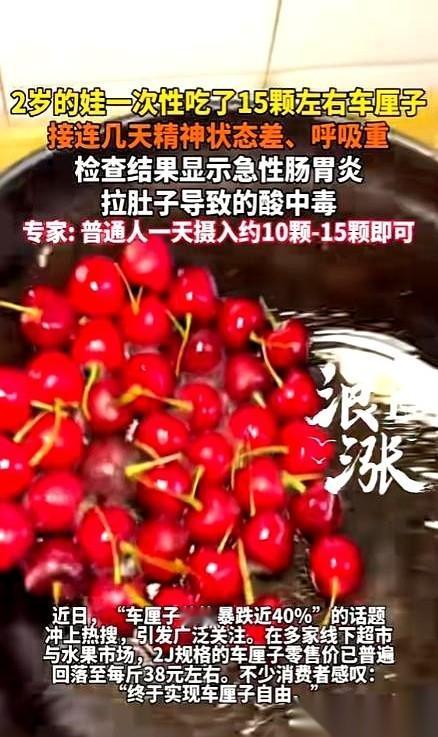


![舅妈突然在家昏迷[惊恐]当地三甲医院竟然不能确定病因哥哥嫂子立马联系了南京人](http://image.uczzd.cn/10975432354583372118.jpg?id=0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