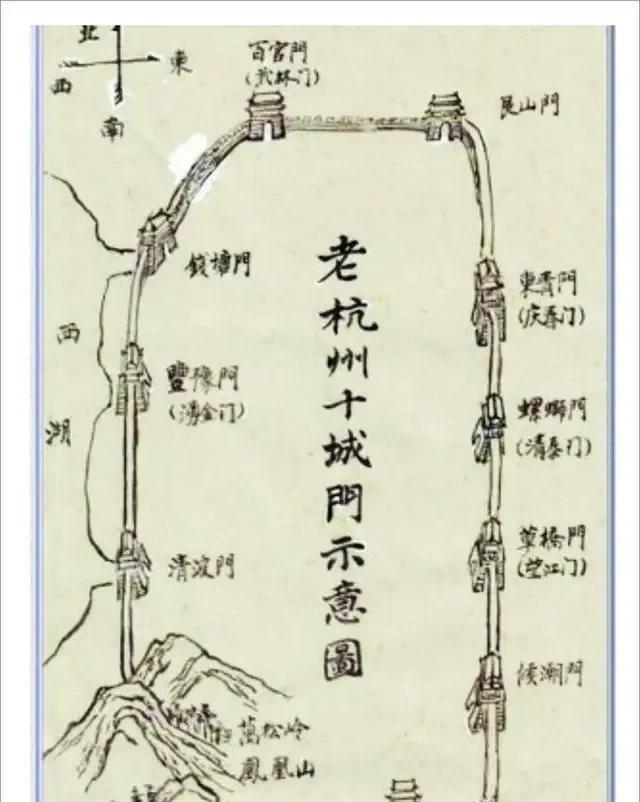1906年,闽浙总督端方参观柏林博物馆时,发现一座石碑很特别。他走近一瞧,惊得目瞪口呆,急问馆长此物从何而来? 1906年初,冬日的德国柏林弥漫着一种严谨而冷峻的气息,在那座历史悠久的柏林民俗博物馆角落里,站着一位身穿清朝官服的显赫人物,端方,这位肩负着清政府考察欧美宪政使命的闽浙总督,此刻并没有在研究德国的律法条文。 而是像被定身了一样,死死盯着一块布满裂痕的石头,矗立在他眼前的,是高昌北凉时期的《沮渠安周造佛寺碑》这通石碑高148厘米,宽92厘米,即便莲花底座尚存,石碑下部三分之一处那道刺眼的断裂痕迹,也在无声地诉说着它颠沛流离的苦难史。 就在四年前,也就是1902年,德国人通过“探险队”的名义,将这块在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沉睡了千年的国宝,连同其他45箱珍贵文物一并打包,这块记载着公元445年沮渠氏皇族崇佛建寺历史的巨石,没能在此后的漫长运输中保全金身。 它在颠簸中惨遭断裂,最终带着伤痕躺进了异国的展厅,对于身为金石学家的端方来说,这种心痛是双重的,他看着石碑上由夏侯粲撰写的近千字碑文,书法高古、佛理精深,这在当时是中国国内都从未出土过的稀世孤品。 然而,此刻它却成为了德国人的战利品,成为了一个关于文化掠夺的巨大讽刺,这种目睹国宝流失的刺痛感,让他在那一刻做出了一个略显执拗的决定:哪怕带不走石头,也要把上面的文字“剥”下来带回家。 于是,一场充满了戏剧性甚至带点荒诞色彩的“复制”行动开始了,端方先是利用自己的外交官身份,同博物馆馆长软磨硬泡,起初德国人严词拒绝,毕竟石碑已经断成两截,哪里经得起再一次的敲打折腾。 但在端方反复的据理力争下,馆长勉强松了口,可惜的是,正是这次难得的机会,因为人为的失误演变成了一场新的灾难,拓印本是个精细的手艺活,需要宣纸覆石,毛毡轻锤,端方自己就是个中高手,但在那种外交场合,封疆大吏亲自撸袖子抹墨显然不合礼制。 他环顾四周,做出了一个让后人咋舌的安排,找了个随行的厨子来充当“技工”,自己在一旁指手画脚地搞遥控指挥,起初,厨师小心翼翼地拓好了一份全本,但这第一份成品在端方眼里似乎成色不足,墨色不够匀称,字迹略显模糊。 追求完美的金石学家劲头上来,忘了物极必反的道理,催促厨师再来一次,也就是在第二次操作中,意外发生了,早已失去耐心的厨子下手没了轻重,只听得一声脆响,脆弱的石碑表层哪里经得住外行的蛮力,竟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文字剥落和碎裂。 这一声脆响,彻底激怒了德国馆长,也惊碎了端方的金石梦,德国人当即下了逐客令,拓印工作戛然而止,最终端方只能尴尬地带着那份还算完整的初稿,以及第二次尚未完成、只拓了四分之一的残本,狼狈地离开了博物馆。 命运的齿轮在这里转动得尤为诡异,这看似倒霉的一天,却在冥冥中为中华文明留下了一丝血脉,端方回国后,视那份唯一的全本拓片为身家性命般的至宝,他广邀海内外的名流雅士鉴赏题跋,甚至不惜重金请朋友以这份全本为底稿。 用复杂的“响拓”技术去补全那份只剩四分之一的残次品,当时的他也未曾料到,自己这番近乎偏执的保护行为,将在几十年后展现出何等巨大的价值,仅仅五年后的1911年,端方就在四川资州的兵变中成为了时代的祭品,被起义的新军斩杀。 但他留下的这两份拓本,却并未随着主人的逝去而湮灭,为了生计,端方的后人将它们转让给了大收藏家李钦,李家人深知此物贵重,甚至专门修建了一座“北凉碑馆”来供奉,将其藏之名山,轻易不示人。 后来的历史证明,那次“厨师意外”得来的拓本,竟然成了绝唱,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,盟军的轰炸机飞掠柏林上空,那座收藏了无数掠夺珍宝的柏林博物馆未能幸免于难,而那块曾让端方魂牵梦绕、即使断裂也要傲然挺立的《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》。 在漫天的炮火中灰飞烟灭。石头死了,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中,而端方带回中国的那张薄薄的宣纸,那个差点被嫌弃墨色不清的“全本”在原碑毁灭的那一刻,原地飞升为了海内孤品,成为了这世间证明那段辉煌历史存在的唯一实物凭证。 历史就是如此令人唏嘘,一群以“保护”和“研究”为名将石碑掠走的所谓文明人,最终让石碑葬身火海,而一个因“失误”和“遗憾”只带回影子的清朝官员,却无意间完成了真正的救赎。 这缕在战火和动荡中延续下来的文脉,在李氏家族手中被小心呵护了半个多世纪,直到1976年,李钦的孙子李章汉在学者史树青的建议下,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:将这份举世无双的拓本全本和那份补全的残本,无偿捐献给中国国家博物馆。 如今,当我们凝视这张幸存的拓片时,看到的不仅仅是北凉的佛法兴衰,更是一段关于守护、遗憾与回归的百年沧桑,一张纸,终究在石头化为齑粉后,替它讲完了未尽的故事。 信息来源:国博馆藏 | 端方旧藏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 国博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