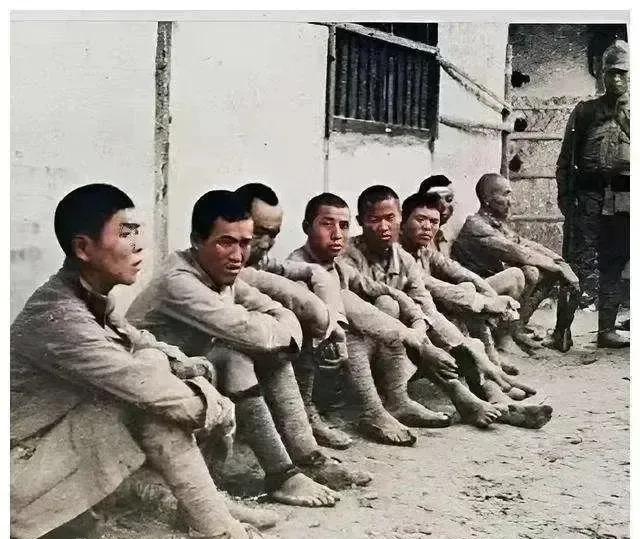1941年,牛子龙杀掉了军统豫站站长,没过多久,上级就找他喝酒,想借机除掉他,牛子龙知道来者不善,却还是赴约了! 酒桌上的酒杯还没碰响,牛子龙已经看清了包间角落里站着的两个黑西装。 他们腰里鼓鼓囊囊的,眼神像钉子一样钉在自己身上。 这种场面他不是第一次见,但这次不同,崔方平的尸体还没凉透,军统特派员刘艺周亲自端着酒杯走过来,脸上堆着笑,手却在桌下悄悄打了个手势。 本来想找个借口提前离席,但转念一想,自己手里握着的东西还没送出去。 那些记着军统豫站与日军私下交易的账本,藏在贴身的夹层里,要是自己出事,这些证据就得跟着烂在土里。 牛子龙当时手心全是汗,他端起酒杯回敬时,故意让酒洒在刘艺周的袖口上,趁着对方擦衣服的空档,飞快扫了一眼门口,那里又多了个穿马靴的家伙,靴筒上还沾着郊外的泥。 这一切的起因,还得从三个月前那张纸条说起。 当时崔方平刚上任豫站站长,就把牛子龙叫到办公室,扔过来一份"日军据点"的地图。 牛子龙一看坐标就心里咯噔一下,那地方根本不是日军据点,是地下党豫西联络点。 本来想当场戳穿,但看到崔方平嘴角那抹冷笑,突然明白这是个陷阱。 他假装研究地图,手指在桌子上轻轻敲出摩斯密码,给门外的交通员发了信号。 三天后行动队扑了个空,崔方平拍着桌子骂娘,牛子龙低着头,心里却清楚,这下算是彻底暴露了。 真正让事情失控的是马丽递来的那张纸条。 这个平时不爱说话的电报员,在食堂打饭时故意撞了他一下,一张揉成团的纸塞进他手心。 "驴使坏,危在旦夕",六个字让牛子龙后背发凉。 "驴"是崔方平的绰号,这意思再明白不过。 他当晚就去找了副站长李慕林,这个老牌军统因为站长位置被抢一直憋着气。 两人在酒馆喝到半夜,李慕林把酒杯往桌上一墩,说干就干。 行动定在三天后的站长例会,牛子龙负责动手,李慕林负责调开门口的守卫。 刺杀那天的细节牛子龙后来很少提起。 只记得崔方平倒下时,手里还攥着那份没看完的电报。 他没来得及多想,抓起桌上的公文包就往外冲,门口的守卫果然被李慕林支去"处理紧急火情"。 跑到巷口时,他回头看了一眼豫站办公楼,三楼的灯还亮着,那是马丽值班的窗口。 后来听说,马丽第二天就被调离了豫站,再没了消息。 刘艺周的酒局终究还是没躲过。 牛子龙知道这一去凶多吉少,但他算准了对方不敢在酒店动手,毕竟自己手里还有账本。 果然,酒过三巡,刘艺周才慢悠悠地说"总部有新任务,跟我走一趟"。 车开到洛阳郊外的监狱时,牛子龙心里反而踏实了。 他被关在单人牢房,每天除了送饭的看守,见不到任何人。 直到1945年夏天,他发现看守换岗的间隙比平时多了三分钟,这才动了越狱的念头。 越狱那天晚上,牛子龙假装肚子疼,把看守骗进牢房。 他用磨尖的牙刷柄抵住对方喉咙,逼问出钥匙的位置。 十多个狱友跟着他一起冲出去,沿渭河跑了三天三夜,才看到根据地的红旗。 后来有人问他,当时怕不怕,牛子龙只是笑笑。 他说最危险的时候不是越狱,是在豫站当潜伏者的那几年,每天早上醒来,都不知道能不能看到第二天的太阳。 建国后牛子龙成了军分区的副司令,后来又去地方搞水利。 当年那些惊心动魄的事,他很少对人讲。 直到1964年病重,他才拉着儿子的手说,做人要有信仰,就像当年在监狱里,就算看不到希望,也得朝着光亮的地方走。 如今在湖南湘潭的档案馆里,还保存着他当年修水库时的工作笔记,字迹工整,一笔一划都透着当年潜伏时的谨慎。 牛子龙的故事,就像那个年代无数隐蔽战线工作者的缩影。 他们没有留下名字,没有军功章,却在看不见的战场上守护着信仰。 如今再看那段历史,才明白什么叫"无声处听惊雷"。 那些在黑暗中前行的人,早把生死置之度外,心里装着的,从来都是身后的万家灯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