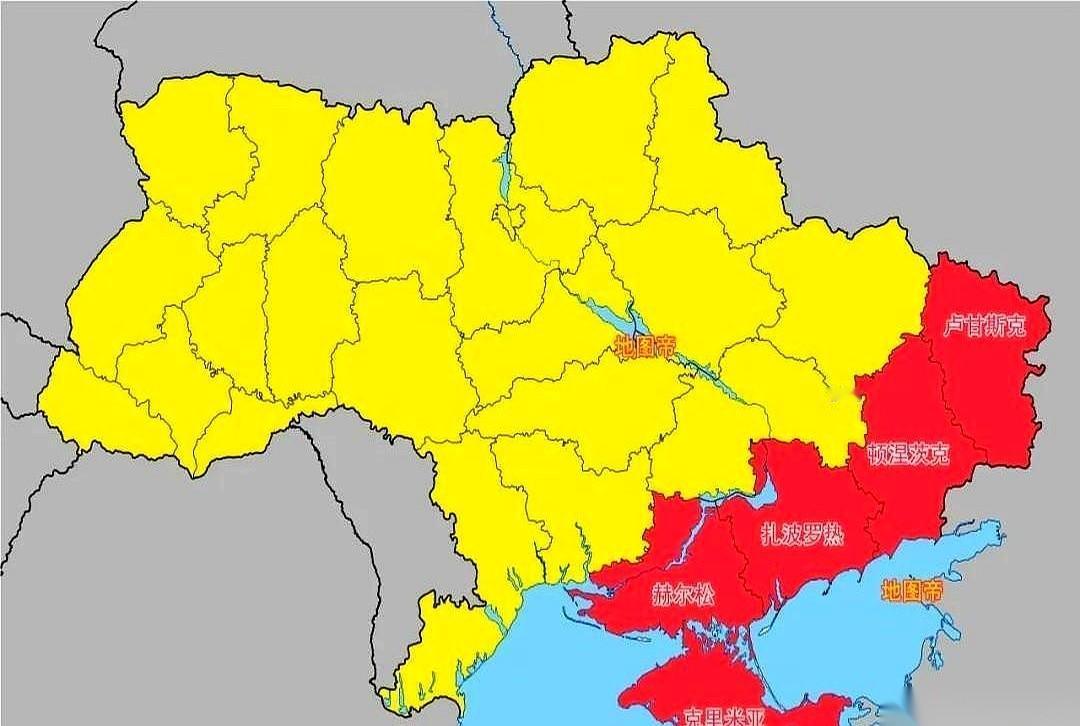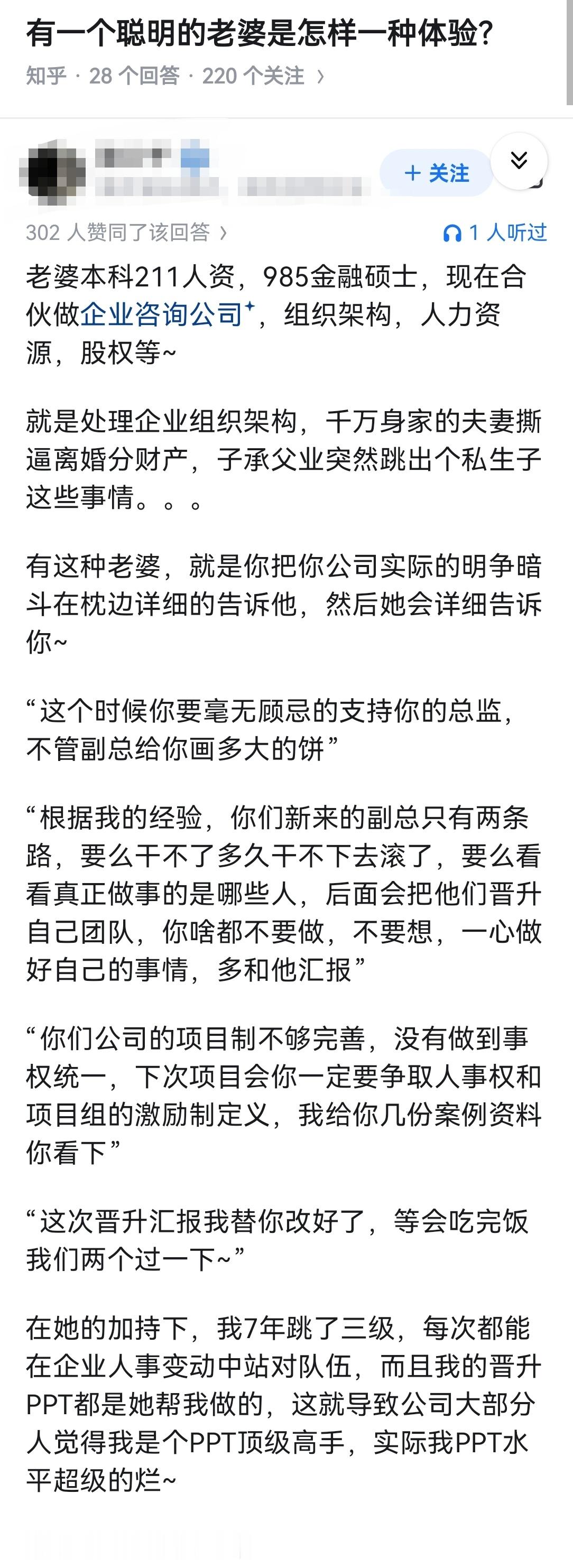2000年的夏天,台北一间老茶馆里,91岁的谷正文坐在藤椅上。 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他布满皱纹的手上,记者问起六十年前的吴石,他沉默了足足半分钟,才开口。 那年是1950年初冬,台北总飘着冷雨。 国防部大楼的走廊比往常更安静,吴石穿着海军中将制服,领口的金穗被雨水打湿了一小块,他刚把一份标着“绝密”的文件锁进公文包,转身就被几个穿黑风衣的人拦住。 谷正文那时才三十出头,在保密局当审讯组长。 别人都说他审人有一套,软的硬的都试过,没有撬不开的嘴。 可吴石被押进审讯室那天,他心里突然有点发沉——这人坐得笔直,手铐在手腕上磨出红印,眼神却像结了冰的湖面,一点波澜都没有。 头三天,谷正文没问出一个字。 他把吴石的官职摆出来,说只要认个错,参谋次长的位置还能坐;又把案卷堆在桌上,说同党都招了,就差他一句话。 吴石只是盯着墙角的蜘蛛,过了会儿才说:“我穿这身军装那天,对着国旗宣过誓,要对得起穿军装的人。” 第五天,谷正文换了法子。 他让人把吴石妻儿的照片拿来,照片是从香港寄来的,孩子穿着小棉袄,妻子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,背景里还有棵开得正旺的紫荆花树。 “你不说,他们在香港的日子不好过。”谷正文把照片推过去,声音压得很低。 吴石的手指碰了碰照片上孩子的脸,指尖抖了一下,可再抬眼时,那点柔软又藏起来了:“我是军人,不是丈夫——军人的本分,是护着更多人的家。” 后来的审讯室总飘着烟味,谷正文一根接一根地抽,吴石就那么坐着,从天亮到天黑。 有时候谷正文突然拍桌子,他眼皮都不抬一下;有时候故意让看守大声骂他“叛徒”,他反而笑了,说:“你们不懂,什么是真正的背叛。” 六十年后谷正文还记得,有次他问:“就不怕死?”吴石看着窗外,台北的冬天难得有太阳,光落在他肩上,像给他镀了层金边,他说:“怕就不做了。” 1950年6月18日,马场町刑场的风特别大。 吴石穿着被捕时那身制服,领口的金穗补好了,只是脸色比之前更白。 行刑的人让他跪下,他没动,反而挺直了背,声音被风吹得有点散:“我是中国军人,死也要站着。” 枪响的时候,谷正文正在办公室整理案卷,笔尖突然断了,墨水在纸上洇开一个黑团,像滴在雪地里的血。 有人说吴石傻,放着中将不当偏要走险路;有人说他是英雄,在最关键的地方替对岸撑住了腰。 谷正文后来审过更多人,有的哭着求饶,有的骂着街反抗,可他总想起吴石——那个连死都站得笔直的人,身上有种他在别人那儿从没见过的东西。 六十年了,他怎么还记这么清楚? 老茶馆的服务员来添水,谷正文摆摆手,指着桌上的茶杯说:“刚沏的时候烫嘴,放凉了才品得出味儿。” 就像吴石那句“我是军人”,当年听着像堵墙,后来才明白,那墙后面,是比命还重的信。 记者要走的时候,谷正文突然又开口。 “他是真正的军人,也是我这辈子最难审的犯人。” 还是那两句话,说得轻得像片羽毛,可落在心里,比六十年前的枪声还沉。 窗外的阳光移了位置,照在他手背上,那些皱纹里,好像还藏着当年审讯室的烟味,和1950年初冬那场没停的冷雨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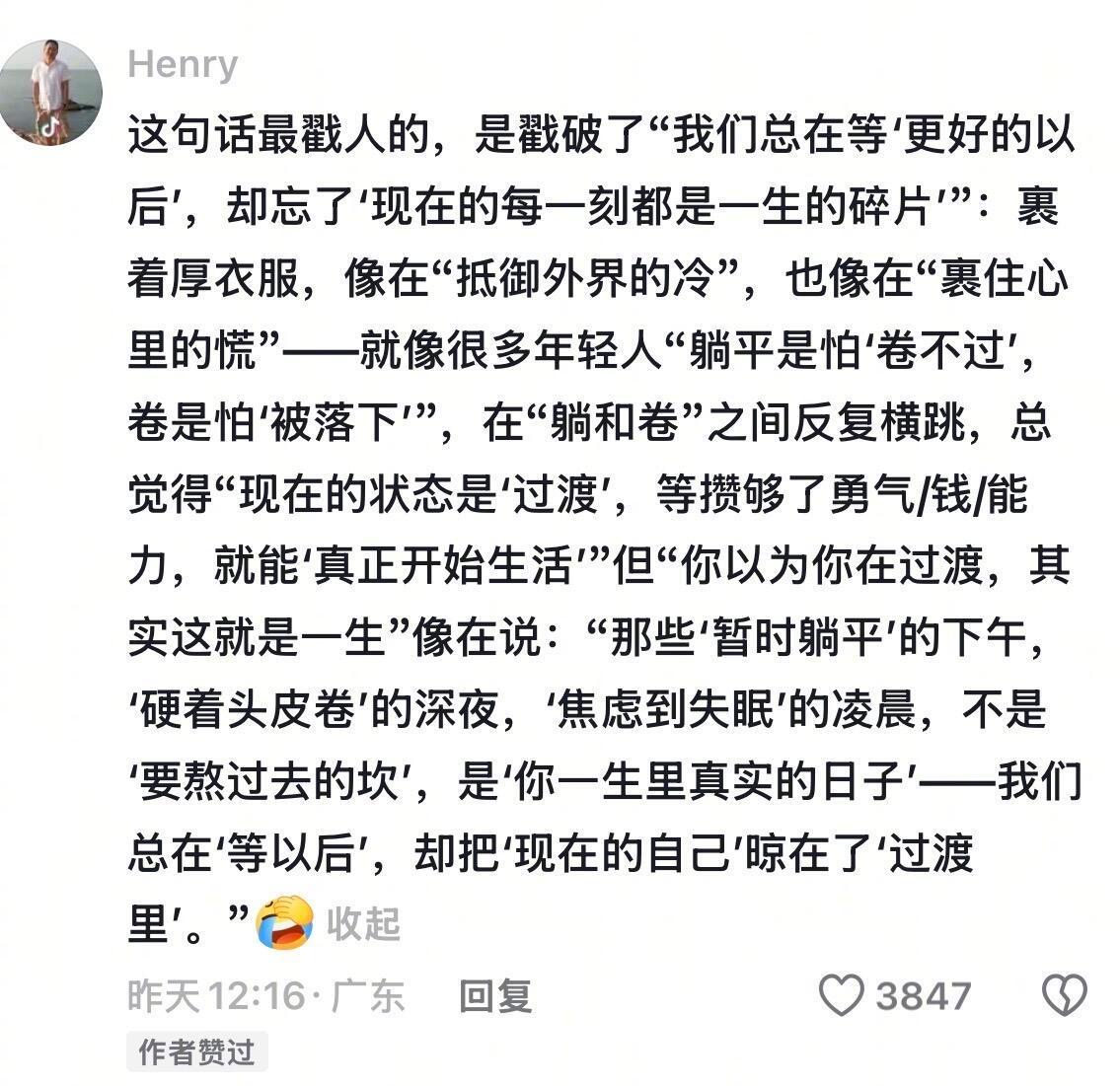
![大部分都是觉得撒泼打滚就能解决问题[吃瓜]](http://image.uczzd.cn/2420963332028313313.jpg?id=0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