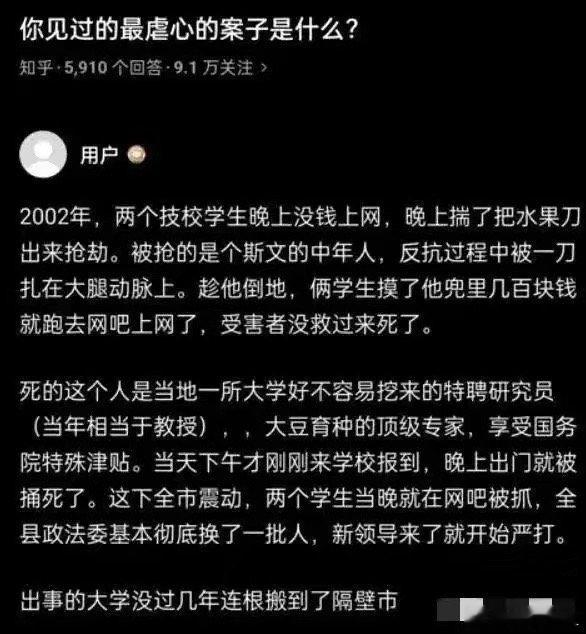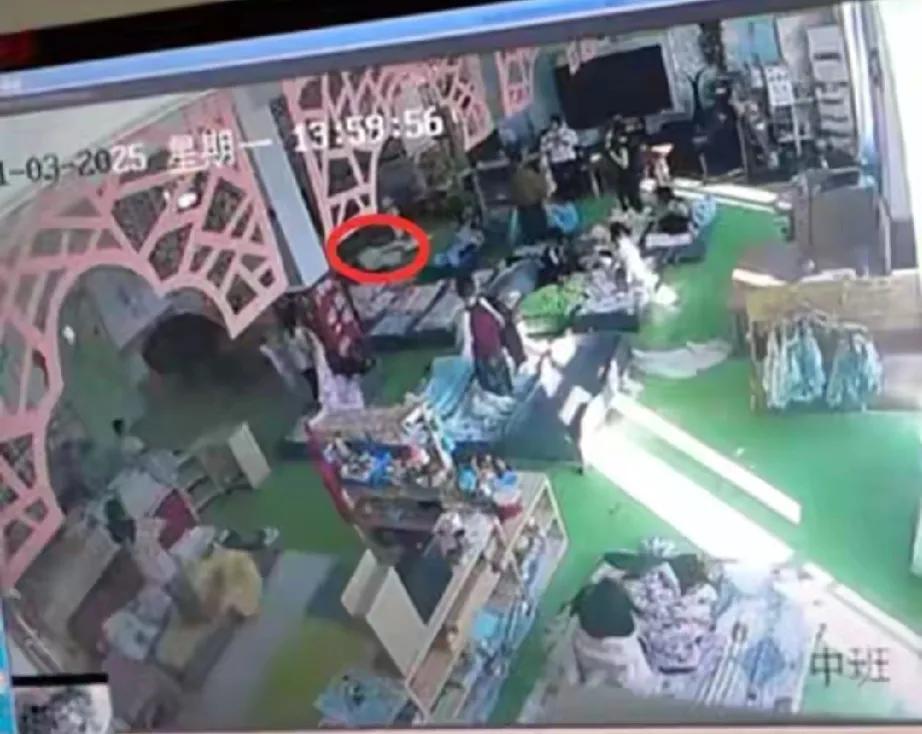这人叫张建军,在一家小公司做销售,儿子今年该上小学了,片区内的学校一般,就想着让孩子进重点小学。他托了好几个朋友,才搭上能和厅长说上话的关系,可厅长那边一直没松口,朋友就提醒他,不如找找厅长夫人,毕竟她管着学校,说话可能更管用。 张建军琢磨了几天,觉得这主意靠谱。他先打听厅长夫人的喜好,听人说她平时喜欢养点兰花,还爱读历史类的书。他就跑了好几个花鸟市场,挑了一盆品相不错的墨兰,又去书店买了一套精装的《史记》,包装得整整齐齐。 九月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,张建军办公室抽屉里的烟盒换了第三个空壳。 儿子小远的铅笔盒上,用歪歪扭扭的字贴着“希望小学”——那是他偷偷从墙上招生海报上剪下来的贴纸,重点小学的名字被他摸得边角发毛。 “片区那个学校,操场都没正经跑道。”妻子昨晚在厨房刷碗时说,水流声盖过了后半句,但张建军听得懂——那是当妈的焦虑,像根细针,扎在他后颈。 他在小公司做销售,手里没什么硬关系,托了三个朋友,才绕到能和教育厅厅长说上话的人。 “厅长那边……不好说。”电话里朋友的声音含糊,“要不试试厅长夫人?她管着基础教育那块,说话可能更直接。” 张建军挂了电话,手指在手机壳边缘抠出一道白印——那壳还是去年公司年会发的,边角已经发黄。 接下来三天,他像侦查员似的打听。 “王姐说,厅长夫人喜欢兰花,尤其是墨兰,说那花‘静气’。” “老李讲,她办公室书架上摆着不少历史书,上次开会还聊起《史记》里的刺客列传。” 信息像碎片拼起来,张建军请了半天假,跑了城西三个花鸟市场。 第一家的墨兰叶子有点卷,第二家花盆太艳,第三家老板蹲在地上给他挑,“这盆刚分株的,根壮,你看这花苞,过俩月就能开。” 他付了三百二,比半个月房贷还多。 又去书店,精装《史记》一套四本,封面是深蓝色烫金,店员用礼品纸包的时候,他盯着玻璃柜里的价格标签,喉结动了动。 约在周六下午的咖啡馆,离厅长夫人单位不远。 张建军提前半小时到,把墨兰放在靠窗的桌子,花盆底下垫着自己带的软布——怕划伤桌面,也怕显得太刻意。 《史记》放在兰草旁边,包装纸的褶皱被他手指捋了三遍。 三点十分,一个穿米色风衣的女人走进来,头发梳得整齐,拎着帆布包,上面印着“教育公平”的字样。 张建军站起来时,膝盖撞到桌腿,发出闷响。 “陈主任,打扰您休息了。”他递过刚买的热拿铁,杯壁上的水珠沾了他手指。 女人接过杯子,目光扫过桌上的兰草和书,没说话,先喝了口咖啡。 “小远……我儿子,今年该上小学了。”张建军的声音有点抖,“片区那个学校,确实……” “张师傅,”女人打断他,手指轻轻敲了敲《史记》的封面,“这套书我书架上有,去年出版社刚送的。” 她又看向墨兰:“我办公室的兰草都是后勤统一养护的,私人花盆带不进去——规定。” 张建军的脸一下子热起来,像被人当众掀开了遮羞布。 他原以为这是“人情世故”,是为儿子铺路的“必要步骤”;可此刻看着女人帆布包上的字,突然意识到——或许真正的“规则”,从来不在这些包装好的礼物里。 他想起小远昨晚问:“爸爸,重点小学的操场是不是真的有彩虹跑道?” 那个问题像块石头压在他胸口,让他忽略了教育局网站上“随迁子女入学政策”的公告,忽略了朋友转发过的“多校划片”文件——那些需要花时间研究、需要跑几趟教育局的路,他觉得“太慢”,不如“找人”来得直接。 这种“捷径”的执念,让他这半个月没睡过整觉,头发掉得比销售业绩还快。 咖啡凉透的时候,女人留下一张纸条:“明天带齐材料去区教育局302室,找李科长,就说是我建议的。” 张建军捏着纸条,手心里全是汗——那盆墨兰最后被他抱回了家,放在小远的书桌上,花苞在灯光下泛着青。 后来他才知道,厅长夫人办公室的书架上,除了《史记》,还有一叠厚厚的家长来信,每封都标着处理进度。 或许为人父母,最该学的不是“走关系”,而是相信规则里也藏着公平——哪怕需要多跑几趟路,多问几个为什么。 晚上小远放学回来,盯着书桌上的墨兰看了半天,突然说:“爸爸,这花叶子好直啊,像不像军人?” 张建军笑了,摸了摸儿子的头,抽屉里的空烟盒,他没再换新的。
丽江女学生失踪案告破:遇难细节披露,蚂蟥肆虐!现场寻获遗体!贵州女大学生丽江独
【121评论】【53点赞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