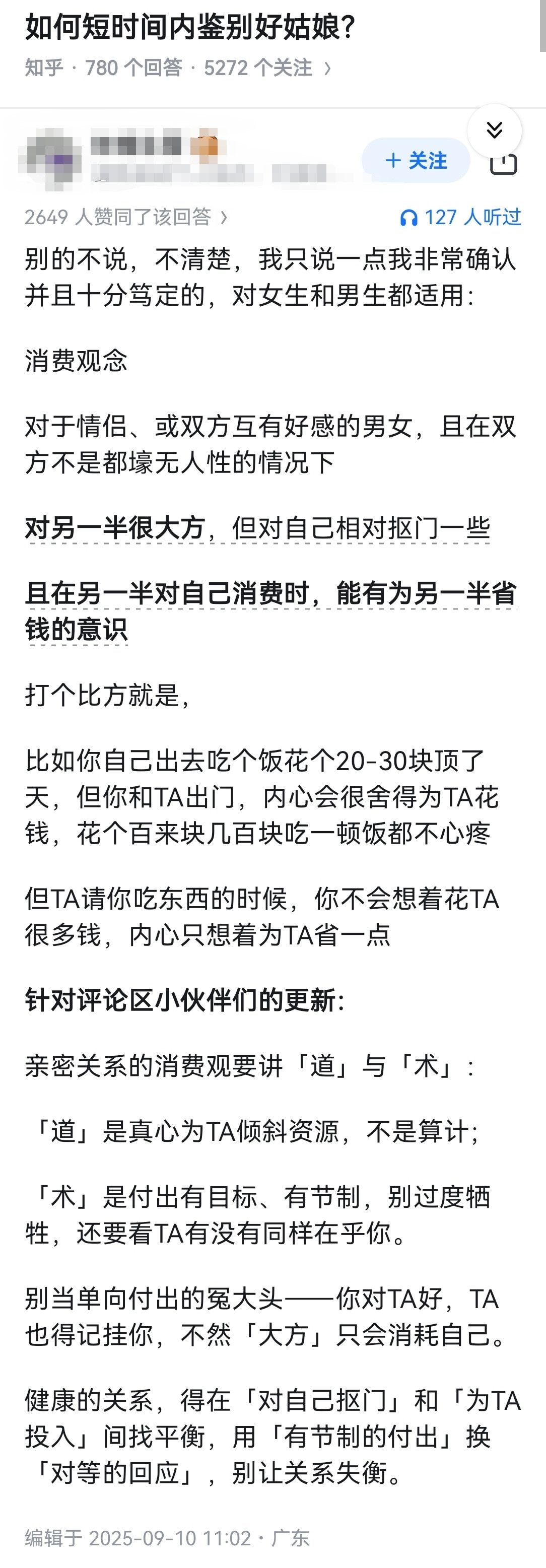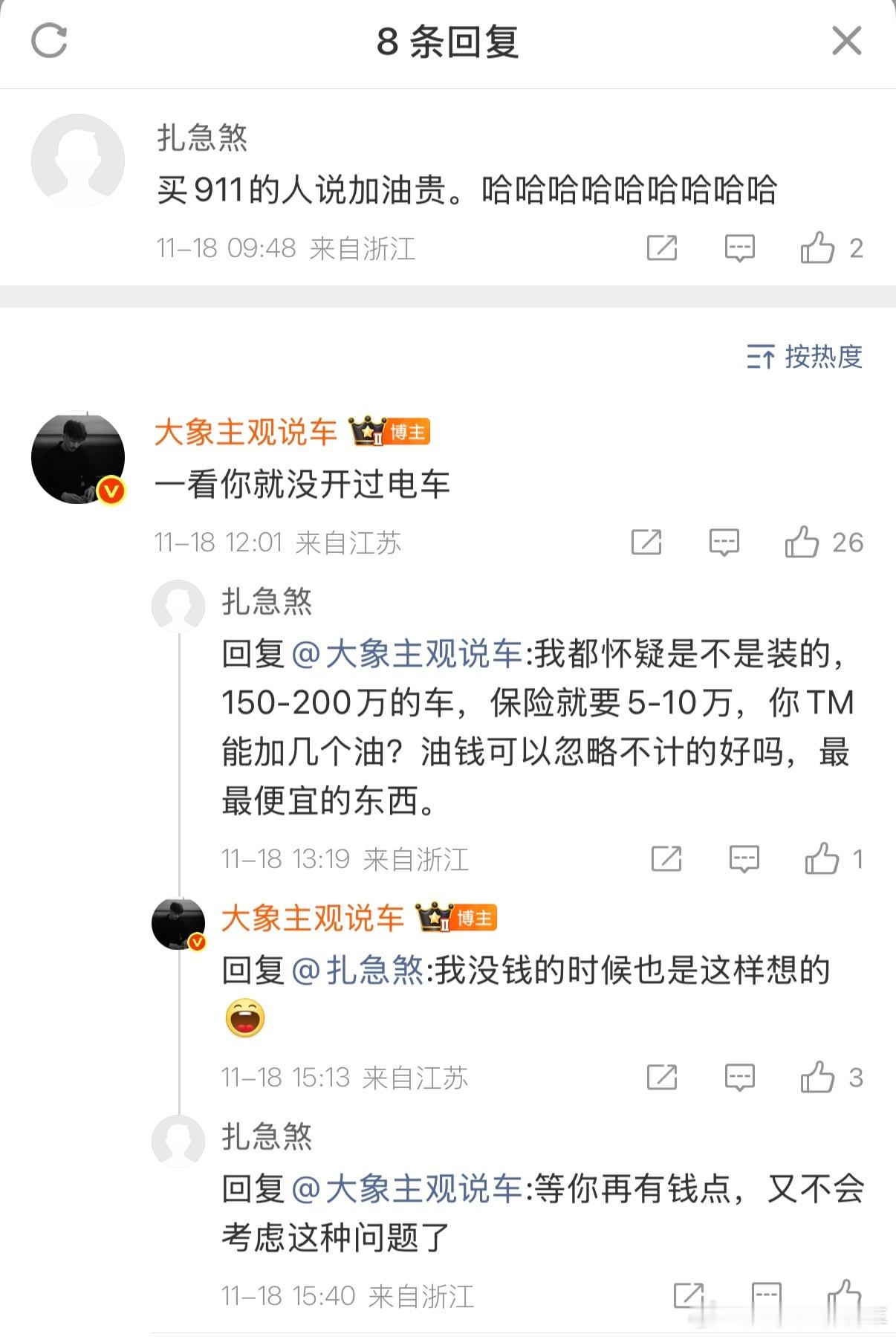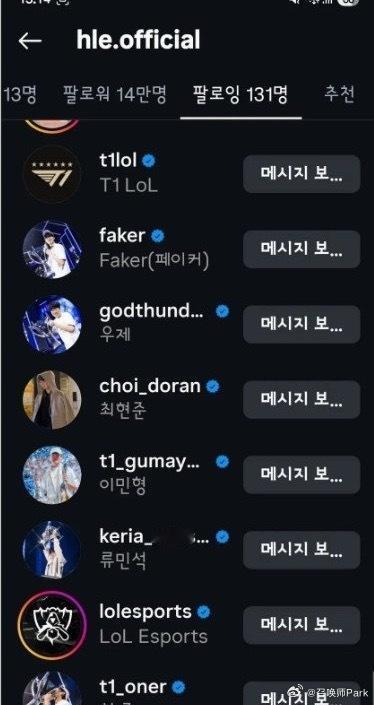我哥大概是疯了。 他把九十多岁,脑子已经不大清楚的老爸,直接带上了他那条上千吨的货船。 老爷子半夜还会迷迷糊糊地想起身,嘴里念叨着,说要去船头“戴缆”。 “戴缆”,这词儿,外行人听不懂。 那是我爹干了一辈子的绝活儿。几十米外,一根又粗又重的缆绳甩出去,“哐”一下就稳稳套住码头的铁桩,船就靠岸了。我小时候站在旁边看,心都提到嗓子眼,可他,从来没失过手。 现在呢? 他连路都走不稳,心里却还惦记着他那份责任,那个他守护了一辈子的船。 其实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。请了保姆,但在家不行。老爷子看不见亲人,一天到晚不说话,人就跟蔫儿了的植物一样,眼看着就垮了。我哥说,不行,得带在身边。 我真得佩服我二嫂。真的。 一个女人,跟着丈夫常年在船上漂,就把那几平米的船舱当成了家。现在,她又把这个家分给了我爸。把里屋最舒服的大床让给爸睡,两口子挤在外头的小床上。 今天她发来视频,正蹲着给我爸泡脚,水汽氤氲的,老爷子脸上是一种孩子气的安详。 我一个大男人,在办公室里,看着那视频,眼泪刷一下就下来了。 那个曾经用一双粗糙的手,撑起我们兄妹五个人天空的男人,就这么,猝不及防地老了。 时间这东西,真他妈的混蛋啊。 又真他妈的,对谁都一样。